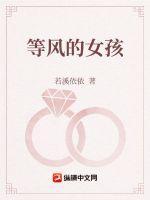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嫁给病弱夫君后 > 3040(第26页)
3040(第26页)
京兆府的林厉繁是站在闻时鸣这一边的。
“就是这些米粮铺子,打着帮官府回收旧币的旗号,让百姓拿成色半旧的假铸币来换取陈粮旧粮。是不是冤枉了,把人扣在监牢里审个十天半月就一清二楚了。”
“林大人何不想想,收假铸币卖真粮食,这么简单的账,无人愿意做亏本买卖。我看米粮铺子才是假铸币的受害者,却被京畿衙门突然扣押。”
少府监特地来的主簿面色严肃地反驳。
“少府监从未提过要钱庄回收旧币,米粮铺子回收这些旧币后到底流通到了哪里,还有待查证。”
他还有更直白的揣测没有说出口,这些假铜钱铸造精良,从米铺调查情况来看,流通甚广,焉知不是米粮铺为假铜钱背书,故意混淆视线,否则少府监早该发现了。
闻时鸣听着两边唇枪舌剑,心中发笑。
原只是觉得那些账目有异常,兼之又碰上假铜钱,想到账面上数额夸张的铜币入账,叫几个小乞丐去打探消息,结果真的发现米粮铺子在大量回收假铸币。
他后续又派了人去乔装打探,再联合京兆府和少府监的人去抓拿。太府寺卿掌财货,此刻多番维护郑家的米粮铺子,正正说明了里头有鬼。
日光被浓云遮蔽了一瞬。
门扉格子上的光线忽地一暗。
闻时鸣看了一旁的铜壶刻漏,已经快午时了,算着马车速度,家中女眷应该早已离开皇都城,在往避暑庄子去的官道上。他默了默,眼前冒出程月圆眼眶泛红,眼皮子有点浮肿的可怜模样。小娘子向来心性豁达,成婚这些日子,他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
明堂里的辩论声一歇,太府寺少卿落败下来。
他面有愠怒,拂袖而去,显然是压不过林厉繁,要去搬救兵了。“京兆府要查,那便好好地查,本官倒要看看能查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
待人一走,闻时鸣就和林厉繁去了监牢。
审了一个下午,刚得出点头绪,京兆府狱卒来讯问室附耳:“小闻大人,平阳侯在咱衙门外,指名道姓要您出去一趟。”闻时鸣毫不意外,毛笔在证词记录上圈了几处,示意林厉繁别放过,出了京兆府的监牢大门。
他父亲闻渊站在树影下,还穿着今日上朝的官服,面上拂过叶缝错杂的光斑,墨丸似的眼珠子朝他看来,凝着几分带兵之人惯有的威压。
闻时鸣站到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父亲找我何事?”
“你这案子,非查不可吗?”
闻渊向来直白,今日对他也无例外。
他两道浓眉皱起来,语声沉沉,“我在朝中听说了。假铸币影响市场物价,归根究底,不是市署直接管辖的责任,你查到这里为止,接下来就交给林大人。你母亲她们都出发了,今日散衙了就告假,别操劳这些事了。”
还是这样,还是不问他的意见,就一锤定音。
闻时鸣拢着衣袖,敛眉之间,心头那股每到此时都有的郁气却并不如想象中浓重,因为他想到了程月圆。只略想了想,如果她还在,会怎么说——
“假铸币骗的是百姓的真血汗钱呀,当然要查!”
“坏蛋就应该被抓起来!”
“夫君想查就去查呀。”
大抵会这样,说的时候,圆圆眼眸里或许还会带了些同仇敌忾,爱憎分明的气愤,把拳头捏紧了。
他心中莞尔,再看向闻渊时,变得心平气和起来。
小娘子的解决之道总是简单直白,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横冲直撞。他耳濡目染,也习得了一些。
“父亲上一次说,荣国公那一家睚眦必报,定会诸多为难,不让我顺顺当当做这份差事。”
他熬了一宿的面上有疲态,却很平静沉稳,“父亲是担心我受伤,怕我被报复,才不让我查下去。”
闻渊一愣,似乎还不习惯他这样亲近的说法。
闻时鸣还未停:“既如此,父亲何不让我借力呢?”
“儿子同荣国公府的是非,自谢御史流放那一次便结下了。两国边境戍卫,从来只有敌不犯我,我不犯敌。哪里会有我安生躲着,敌人便对我敬而远之的道理。”
“父亲说大哥有能力自保,我没有。”
“可我,是当真生来没有吗?”
闻渊眉心蓦地一跳,“你这话是何意?”
闻时鸣将手伸出树影外,躲得苍白的皮肤在阳光下才能镀上暖色,“当年意外落湖后,每一位来看诊的御医都告诉父母亲,我要静养,忌劳苦,忌风寒湿冷,不可再习武耗费本就不多的气血,是以我衣食住行样样矜贵,有时甚至错觉,自己像平阳侯府的一位女郎。”
闻时鸣收回了目光,落到闻渊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