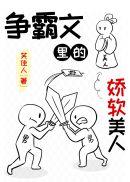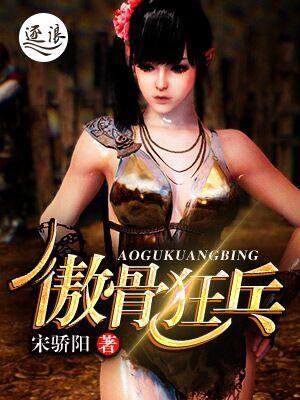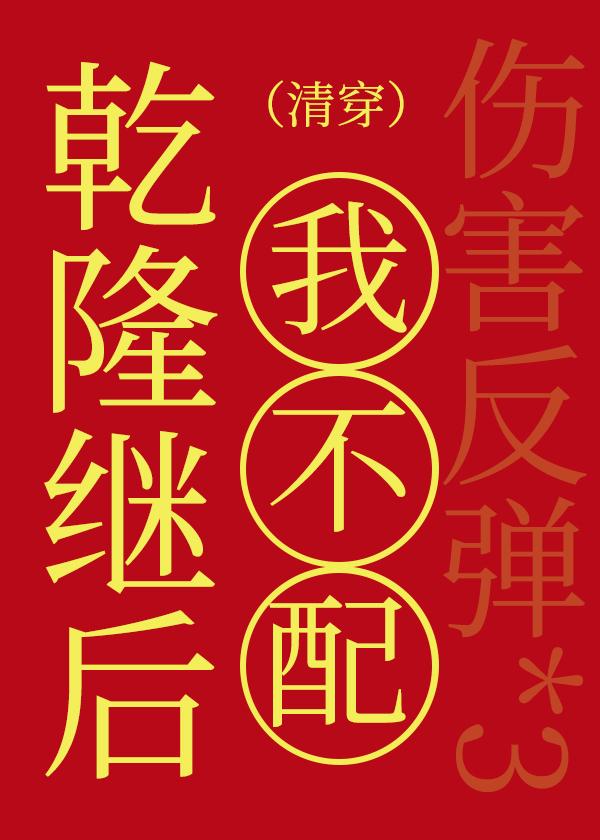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233章(第3页)
第233章(第3页)
为了对付工会,她推动了新的法律,设置了各种条件,实际上让英国的罢工,几乎得不到法律的批准。
从分配的角度看,其实撒切尔夫人,就是从原来西方为了避免苏联意识形态吸引力,而有意对劳动阶层的让利(高福利)上撤退,把分配向资本家倾斜,由此激发他们的投资积极性,同时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经营效率就这样上来了。
过去的高福利政策,有效地遏制了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的蔓延,但代价则是对资本家的高税收,需要他们做出“牺牲”,缴纳高税收,来维持民众的高福利。现在撒切尔认为这一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需要反其道而行之,让资本家的积极性高起来,对民众的剥削程度加大,才能提高效率。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内卷”,大家能吃的肉,太有限,现在认为必须让资本家多吃,民众少吃,以后才有更多的肉被生产出来。不要去管未来要如何解决总需求的问题,先解决供给的问题,让供给有可能加大。他们认为,供给加大,可以带动就业增加,然后带动消费增加,形成良性的循环。
原时空撒切尔的这套保守主义策略,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号称以“资本主义的活力氛围,成功地取代了工党社会主义的颓靡氛围”,其实工党有个鬼的社会主义,最多叫做“费边主义”。西方的吹嘘是,把民众的自由,归还给了公民,让民众自己养活自己,用自由竞争来代替了政府干预与管制。
从这个时刻起,在经济主流上,盎格鲁开始用超发货币的货币主义理论,代替了几十年来以政府干预政府投资为特色的凯恩斯主义。
有趣的是,明明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但西方开始吹嘘这是“保守自由的主义”,本来对立的两个概念,变成了统一体。而传统大政府的凯恩斯主义,变成了权力主义,地方政府权力大嘛,撒切尔大大加强了中央的权威主义,但他们大量削减了地方的权力,过去与现在,变成了“权力到自由”的转折。或者未来的西方话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高度发展的。
在撒切尔的治下,几乎一切都被划入了私有化的范围。首先是小企业、小团体(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私有化,政府在这些小企业、小团体拥有部分或绝大部分的股份。之后紧接着便是“天然”垄断行业,例如电信业、能源、航空业。卖掉一切后,英国获得一笔巨大的资金,暂时覆盖了巨大数目的失业救济金,撒切尔时代,英国人曾经有300万失业,而全国人口不过是六千多万。
但未来这个政府,就要靠私人企业的税金过活,政府的力量,其实是衰减的。国民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变成了股东,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变成了资产和所有权的关系。随着公共部门领域严重遭到忽视,贫困人口日益增加。
本质上她摧毁了英国几乎所有的工业力量,制造业几乎彻底崩溃,英国成了一个依托于旅游业金融业这种空中楼阁的国家,经济自主权进一步崩溃。私有化的各种国家产业,不但价格飙升,而且使英国政府和人民,几乎彻底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
在李思华看来,撒切尔的改革,是饮鸩止渴,原时空如果不是苏联先崩溃了,恐怕英国早就崩溃了,制造业大萎缩,靠依附于美国的金融吸血过活,怎么可能长久?是苏联崩溃的红利,养活了后来的英国,拖到2020年后,李思华认为这个国家,重新回到了本就该崩溃的老路。
新时空的条件完全不同,最关键的一条是,西方的市场空间大为缩小,现在英国贸易和金融服务业的市场,相对原时空是大大缩小的,中国与英国,只有产品贸易,金融服务上几乎不往来,使得英国没有东亚市场;苏东、西亚、非洲、次大陆、甚至半个南美,主要都是中国“货币互换”之下的产品市场。
英国的金融服务业,越来越限于欧洲和越来越少的英联邦国家,这样的市场空间,相对原时空的缩减,恐怕至少是半数,这就使得英国的产业调整,被迫“螺蛳壳里做道场”,腾挪的余地大大缩小。
例如,英国国企股份资产换到的现金,由于估值下降,会大大减少;市场空间小,资本家接手后的规模小、利润少,导致税金就少;而由此转型扩大的就业就更少,于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反而需要支付更多的失业救济金,这必然导致政府只能像美国一样,依赖更多发行国债,可是英镑的信用,早已比不上美元,这就只能导致英镑不断贬值。
所以新时空英国的这套新政策,完全可能导致恶性循环。政府的资产出售收入和税金收入,远远比不上每年需要的社会支出,只能导致救济型福利不断减少,于是贫困人口日益增加,社会变得动荡。而随后的债务增加,导致英镑贬值,会让上述问题不断严重化。
不具有原时空的条件,同样的政策,完全可能导致“良药变成砒霜”,撒切尔政策,本来就是牺牲民众成全资本家,让底层社会变成“压力驱动型”劳动阶层,可是如果处理不好,底层社会只会变成“躺平型社会”,如果躺平不了,就会变成“冲突性社会”会。而这种结局,就是李思华想要的。
李思华每一次想到撒切尔夫人的某些方面,总是摇头,认为她是一个被资本主义高度异化了的人物。例如,如果看到有人生活贫困,她的第一反应绝不是同情,而是指责对方不够努力,无论对方如何证明自己,她都会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作为反证,且对这些“不够努力的人”,充满了怒其不争的愤慨。
殊不知撒切尔能从平民,进入牛津大学,再到议员,最后到首相,这种偶然性有多大。她无法理解,底层多数的人民,无论如何努力,也不会有她的智力天赋与幸运值,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撒切尔的名言是:“每一个人都有按他意愿工作的权利,有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有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有把政府当作公仆、而不是主人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是英国的传统,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实质。”
语言很漂亮,但是底层人民,有几个人能找到符合自己意愿的工作?那点可怜的收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就不错了,这算是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太可怜了吧。私人财产不过是虚幻,而除了选举时的麻醉,他们真的能把政府当作公仆?
无论如何,在新时空,英国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帮手,所以击溃英国,是重要的战略目标。撒切尔的改革,正好是一次努力的良机。
所以李思华精心构筑了针对英国新的三重系统打击策略。
第一击,是与法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新时空发展到现在,美国和美元的影响力相比原时空是不够的,对法国这样本来就有较大独立性的二线大国,就更是如此了。
虽然中法两国在非洲过去有着激烈的角逐,但时过境迁,法国失去的已经彻底失去了,而中国向法国表示了不会介入北非五国(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的态度后,深悉“胳膊扭不过大腿”的法国,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最近2年,两国已经恢复了完全正常的经贸关系。
在美元不断贬值、中国的出口商,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美元的背景下,法国愿意接受“法郎-人民币互换”的意愿高涨,实际上欧洲美元主要是通过英国这个金融二道贩子,法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法郎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没有货币互换,中国人能接受的有限——法郎也在不断贬值呀。
如果法国人有足够的人民币,从东方进口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那就是比使用美元要便宜1%2%,这是中国近年来有意形成的差价,作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这样的价格控制,否则市场汇率将自动调整。
所以实现“法郎-人民币互换”对法国是有巨大利益的,而且在美国控制的SWIFT跨境汇兑货币体系之外,相当于法郎有了一个另外的币值稳定工具。这让法国人的积极性很高。
预计这个货币互换协议将在今年(1979)年底签署。而以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之后就可以突破欧洲大部分国家,例如德国,还有意大利、西班牙等欧共体除了英国以外的全体国家,这就使得英国作为欧洲美元金融中心和二传手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变相降低了英国金融业的重要性和收益,其实也是对美元的一种打击。
第二击,是计划影响1982年的马岛战争和爱尔兰共和军。
中国与阿根廷的关系属于正常,会在最近3年内,影响阿根廷增强对英国针对性的军事力量,例如设法加强它的空军和空射导弹,包括岸舰导弹力量。这将导致,最终英国即使仍然能打赢这场战争,也会损失增大数倍,完全影响英国的国际地位,以及撒切尔因此在英国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她在国内地位不稳,英国政府的政策推行就会充满矛盾和冲突,使得英国内部的内耗进一步加大。
阿根廷缺乏外汇,但绝不缺乏资源,按照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阿根廷对购买中国武器弹药,具备足够充分的购买力,不用外汇、用矿产抵消就可以。例如阿根廷丰富的铜矿、锂矿等资源,利用联合开发的模式,不难让阿根廷提供足够支付的矿产。甚至还有背后中国“顾问”可以提供的针对英军的军事策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