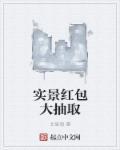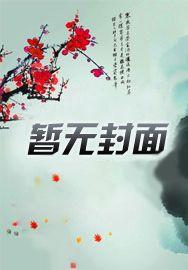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205章(第1页)
第205章(第1页)
李思华把这个新引擎,叫做“产业金融工具”,她觉得前世的叫法,太拗口了。
她还记得当时她与史政福讨论的时候,史政福问她:“这个工具,似乎与现在的混合制央企的资本金制度,有一定的关联?”
当时她的回答是:“是的,所以产业金融工具其实是双引擎。混合制央企,基本上是国家投资的某项科技获得突破,并确定具有大的商业化价值的前提下,由国家基金投资,形成混合制企业,例如华为通讯,所以参与的科学家、管理层和员工,虽然在不出资的情况下,享受35%的工作股,但其实这种股权是受限制的。用西方金融的角度看,这大致相当于一个风投中,天使投资的阶段。”
“当然混合制央企,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模式,比如民间研发出了科技,国家基金投资,也是最后形成类似的格局,这都是天使投资阶段。”
“但现在的产业金融工具,这是对应后继的大规模产业化阶段,例如华为在全国推广百万门程控交换机,这个项目就可以利用产业金融工具,混合制的华为,仅需准备15%的资本金,就可以启动这样的项目,这当然会让推广的速度大大加速,也就让华为成长得更快。”
“有了这个产业金融工具,再配合前半段的混合制资本金制度。那么在关键的产业发展和推广上,我们的金融体系就算是齐活了。”
史政福当时的说法是:“其实还不止,还有风险投资体系作为补充。不过,对风投体系不可太过高看,国家的风投基金还好点,民间的风投基金,这些年观察下来,主要多是追求短期的回报,超过三年都很够呛,最好是当年就有回报,能坚持到5年以后再说的很少。”
“毕竟都是私募资金,每年都要给投资人表现,否则就可能导致撤资,这是有先天缺陷的,只适用于赛道特别明显、短期成功率很高的项目,或者说,就是那些能在短期上市的项目,至于这些项目的长期前景,真正关注的风投基金不多。”
李思华也同意他的看法。她从前世的经验来看,美国的风投体系,在孵化美国的明星企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不是没有缺陷,史政福的总结是精到的,最大的缺陷就是关注短期,追求的是泡沫的大小,泡沫越大收益越大嘛。所以碰到互联网这样的产业,效果就特别好,因为故事好讲,泡沫可以吹得非常大,而且企业易于上市取得高市值,所以风投基金与互联网企业是绝配,其它的还有生化领域,也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风投体系,在其它“冷门”科技产业孵化上,就很不好,例如原时空中国领先的舰船综合电力技术(马明伟少将团队的发明),实际上是改变船舶动力系统的伟大发明,在商业上的前景,也不可限量,但美国一直落后,追了很多年也不行,甚至影响到了福特级航母。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也是只能靠国家投资来搞,而美国冷战后,国家在科技上的投资是有限的。
如果美国的私企,有投资这样耗资巨大的新科技,几乎不可能拿到风投的资金,因为这既不是短期的“好项目”,也很难吹起巨大的泡沫。
所以她对风投体系的看法是,风投很有用,但不能神话,尤其是那些难度巨大、周期长的核心科技项目,是不能依靠风投体系的。
李思华此时并不知道,后来到七十年代中国ICT行业横扫世界后,西方企业和财经界,普遍注意到了中国的科技金融引擎政策,被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产业金融三叉戟”,这个称呼本身就代表着敬畏,因为三叉戟是海王的权杖嘛。
西方各界,都对中国的产业金融政策做了仔细的研究,发现除了风投体系大家本来就相似以外,其余的“产业金融前后双工具”,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无法模仿,因为他们的“小”政府,根本无法执行这样的政策,否则就是要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了。
西方包括美国在内,在产业政策上,也只能在减税上一去不复返,然而减税,就意味着国家的收入比例越来越小,军事和福利上又不能减,债务只能逐步走高,而政府因此在经济上的调整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圣阅读着关于“产业金融工具”在全国推开的调研内参。
过了一会,他放下文件,内心很复杂。他不由得站了起来,到门外的小院里踱步思考,有一点挫败感,这一次他努力的方向,相当于被中央否决了。
他并没有能看到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兴起的势能,但是此前注意到了六五计划的经济动力可能不足的问题,当时作为副总理的他,提出的策略,正是逐步地放开商品房市场。
理由是很充分的,建国27年的发展后,房地产形成了组屋和商品房两个市场,而国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小富人这个群体并不小,商品房现在的售价,是组屋的10倍以上,太过昂贵,制约了商品房市场的发展,如果在土地、税收和贷款上,给予一定的优惠,这个市场就会蓬勃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动能。
多年的研究下,他不是不知道商品房市场,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但地方政府其实很支持,能够为地方带来更多的收入嘛,道理很简单,本来一块地卖1000万,现在卖500万,似乎少收益了一半,但现在可以卖掉4块,总收益是2000万,多了一倍。
对于商品房市场发展而因此带来的负面效果,他是认为“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大于弊就行。对于中央担心的资本主义化的发展,他是不以为然的。
但总书记代表的中央,显然不认可他的意见,在否决了商品房市场发展的策略后,是从一个他从未想到的角度,用科技产业的金融引擎,替代了商品房金融引擎。
从他最近的研究看,这个策略非常高明,而且效果应该是显著的。这一段时间他自己的调研和研究确实表明,这是个超级的大行业,总书记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恐怕确实是当之无愧,这样的产业,其在经济上的带动性,不言可喻。至少20年内,其对经济的带动效果,不会逊色于商品房市场。
这让他内心不免有一些挫败感。他看了看雾霭层层的天空,不由叹了一口气,自己都已经62周岁了,再有3年,到1969年,就必须退休。这就是结局了吗?
第326章城市与老干部的未来
李思华头戴安全帽,在郑州市委书记和市长的陪同下,亲自下到地下,考察地下物流和地下管廊的建设情况。
新中国从二五计划开始,新城市建设就要求城市市区的道路,必须是三层架构,最深的地下二层的城市管廊,地下一层的物流通道,以及地面的交通道路体系。当然不是所有的道路都必须如此,但只要规划要用管道和物流必须经过的道路,那就必须这样做。
在新城市,这样做不算太困难,因为每条道路,都是新建的,无非是挖得很深,最深的地方,可以下到地底18米左右,然后有点类似建筑三层的房屋那样,混凝土钢筋浇筑建构起三层的结构,使得每层都有足够的承重结构,然后做好各层隔离、封闭和防水。每隔一段距离,都有进出口预留。
这样实际的一次性建设成本,当然比较高,如果与原时空一条典型的城市道路相比较的话,李思华估计成本至少是翻倍了,但长期下来,尤其是管廊走道,避免了维修的大难题,长期是更经济的。
好在这些年,中央还始终保持着一定的“价格扭曲”能力,就像组屋体系一样,市政体系尤其是地下体系建设,仍然可以最低成本化,所有的钢筋水泥等大项物资,采购价都是最低的。这节省了不少成本。所以整体上,全国都是咬牙按照新规划,来建设各地新城市。
而各个城市的新城区,按照“标准市”的规划原则,也是如同新城市那样,直接建设三层道路体系。但那些老城区的问题,可就大了,每改建一条路,这条路就至少要废掉大半年,而且事先还必须要所有的管道,能够临时性地“改道”,避免影响城市一部分的生活和生产体系。至于对交通的影响,就更不要说了。
所以一直到西元1960年,全国都是实行的“双轨制”,新区按新法,老区按老法。老城区就只能是按照过去的做法,要维修或者新建某条管道,就对道路“开拉链”,有的时候一年甚至要“打开拉链”七八次,这显然对城市造成了很大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