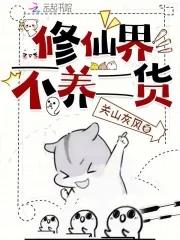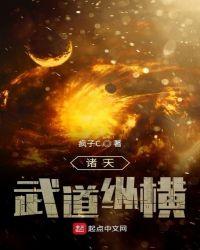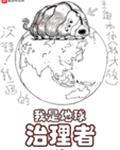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204章(第3页)
第204章(第3页)
原时空的金融引擎是房地产,用房地产“金融变现未来”,房地产兴旺,再带动其它行业;房地产上发了财,再去消费其它产品。这在前期二十年,非常有效,但后期就逐渐一地鸡毛,各种后遗症,估计几十年也消不掉。
所以在新时空,她一早就摒弃了将房地产,作为主要的金融引擎,而是利用强大的初期资本,直接以产业作为经济引擎,其实是去掉了金融作为“杠杆工具”,对经济的驱动作用。牺牲了一些效率,但让经济走得更稳更健康。
其实这很好理解,如果说社会本来的投资是1,但通过房地产的上涨,“可变现”的投资,就可能变成了3,其中2可能变成了消费,而1仍然是对其它行业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强了不少嘛。
所以金融杠杆仍然是有作用的,不用房地产,有没有可能有其它副作用较小的金融杠杆工具?
如果不考虑私有民营经济和私有成分比较大的混合制经济,单单考虑国企,是谈不上什么金融引擎的,银行和企业都在国家的手里,杠杆率还不是取决于中央的决定?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到去年即1965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民营私有经济,已经占国民经济的很大比例,其中资本大约占了22%左右,而创造的GDP高达29%左右。这个比例,还是剔除了国家入股的混合制企业的结果。
所以第一,必须一碗水端平,不能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包括金融条件;第二是对金融引擎的需求性逐渐增强,尤其是国家比较关注的混合制企业,多数都是在前沿产业即高科技产业,这部分,可以说是国家的未来,需要有一种强力而又有所谨慎的金融引擎。
大约在十年前,李思华就有了对今天这个金融引擎的初步设想,这种金融工具,正是她穿越前的2022年,国家开始试行在房地产歇火后,新的金融引擎模式,有个拗口难懂的名字,叫“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普通人可能听得一头雾水,但用个例子来解释就很简单,例如某个项目,本来要求的是自有资金30%,然后银行配资70%,杠杆就是3。33倍;但如果使用这种新工具,就可以让企业只要准备15%的自有资金,其余的15%由国家银行成立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计入资本金,然后企业仍然可以在银行贷款70%,所以杠杆率就放大到原来的两倍,变成了6。67倍。
这个金融引擎的厉害在于——等于国家亲自下场,来做重要项目的投资人了,还帮项目介绍贷款,一条龙服务,当然真的是一个强大的金融工具。
而且它的投资原则是“保本微利”,国家投资机构,只做财务投资,行使股东权力,不参与项目的实际建设运营,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退出方式。
这个引擎,在10年前的作用,并不会太大,因为那个时代的产业,高科技的项目太少,大项目都以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为主,所以时机不成熟。但现在,完全成熟了——正好是电子信息产业的爆发期到了。
中央虽然已经建立了几十家最关键的电子信息混合制企业,但这个领域哪里够?起码也会诞生超过10万以上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那么刺激的金融手段是什么?就是这个引擎。
李思华前世是通讯军官出身,对于这个领域是最精通的,而且没看到猪跑,还没见过猪肉吗?很多项目,只要报到她那里,就会刺激她已经淡漠的记忆——她知道原时空,后来哪些产业发展起来了,哪些产业是最有价值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国开行和农发行等做初审,最优质或者拿不准的项目,让她亲自过目一遍,先把1000亿元发下去再说,这1000亿元能够带动6000多亿元、在电子信息行业为主的新投资(按照6。67杠杆率),这在六十年代是什么力度?可以说,这波投资下去,中国在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关键的电子信息领域,领先美国就稳了。
未来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其实所有的货币,都属于一种信用货币,钱本质上是通过举债,加杠杆而印出来的,但理想的信用货币,必须找到实体经济当中,某些个也在膨胀的产业,跟你印钱的这块对应起来。原时空是后患巨大的房地产,而新时空,她是采用了先进产业来对应。
电子信息即ICT产业,未来是一个数十万亿元规模的超级产业,这才能承受得起货币的杠杆作用。
李思华当年和史政福商量,对企业一早就采取了资本金制度,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混合制企业,都是一视同仁——你自己必须要投一部分钱,才能找银行借钱,用来防止某些人空手套白狼。即使是国企,也要由国家出资本金。
当时她并没有告诉史政福,其实她已经预留了当下采用这个新金融引擎的余地。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外,中国就有了一种独特的工具,来调整各个行业的投资力度,想要限制特定行业,就会提高资本金比例,反之就会放松比例。现在做的,就是对ICT和其它一些特定行业放松比例。
这个工具还预先防范了一种风险,那就是资本水龙头的控制权,并不在地方政府的手里,而是在中央意志直接监管下、遵循市场机制的中央政策性银行手里。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这类项目,反而必须努力为提升当地的整体经济环境而服务好。
这是彻底地以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金融循环,替代掉所谓的土地财政。整个循环从国家组织的投资基金开始,大力投资高科技,就如同现在的ICT行业;再用基建等途径,为这些产业打通应用市场,比如普及电脑和未来普及手机,有必要的时候会为这些投资,打造新的金融工具,确保资本向这些方向流;然后就是打造市场,甚至可以发消费券,给定向补贴,贴扩大这些产业的终端市场;最后则是完善金融市场,推动这些企业快速上市。
整个的基础链条是“投资科技-基建普及-扶持市场-上市回笼”的循环。这些企业上市和业务发展,市值膨胀,随着ICT产业的壮大和科技的发展,以及GDP规模的膨胀,国家信用就可以同样膨胀,有更多的能力印钱举债,投资更多的项目,形成越来越强的金融循环。
这样的一个模式,李思华个人认为,远胜于土地房地产的模式,因为金融推动的产业发展,是高质量的,而不只是过多的建筑垃圾。这是真正地壮大了实体经济和科技含量。
除了ICT行业,在必要时还可以在基建领域等进行,例如今年开始的高速建设,以及1970年以后,逐步开始的高铁建设,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松动资本金,让高速和高铁建设更快地发展。
这是这些年,她心心念念要实现的新金融引擎,现在终于到了完全可以实施的阶段,最近她亲自批准的项目,就有超过1000个,这让她感受到了很久没有的快乐——挥金如土。
按照此前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计委研究部等的预计,从1966到1967年的中国“六五计划”期间的GDP增长速度,可能在8%左右,在他们看来,经过了27年的高速成长,确实增长的速率不可能太快了,毕竟基数已经太大了嘛。
结果李思华就抛出了这个新工具,要求增长速度,需要仍然维持在接近10%的水平,不是这样长期的高速增长,我们如何把美国和苏联远远地抛到后面去?老娘脑袋中的工具,还不止这一个呢。
1000亿资本金投入,引导6000多亿的高质量投资,意味着5年可以翻一倍多的话,相对于没有这个工具前的投资效果,至少要多了30004000多亿的收入,1965年的GDP是3万亿多,也就是5年后至少要比原来的预计,多了67%的GDP,摊到每一年,相当于多了一个多点的增长率,而且还没有计算附带的辐射效应。整体评估下来,妥妥地能拉动经济,每年多2个百分点左右的成长。
而对于ICT行业的爆发增长,所有的高层经济工作人员都是看好的,也因此对这个计划非常看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融工具!
所以当初李思华在相关的会议上,向经济高层们,讲清楚这个新的金融工具和它的模式后,立即引发了轰动,大家一下子都找到了着力点,尤其是金融口的领导同志们——虽然国家不让金融赚钱,是保本微利,可是有企业上市的话,这些股权,不就可以盈利的吗?虽然这是抛售后,再重复变成新的资本金,但这个政绩多好看呀?
这个工具,立即得到了高速的启动,大量的项目,经过计委等部分的筛选,如同雨后春笋般地递了上来,甚至很稳定的股市,也上涨了一波,大家对于ICT产业的前景,都充满了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