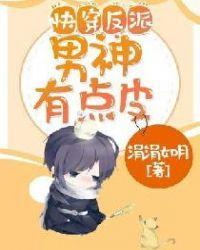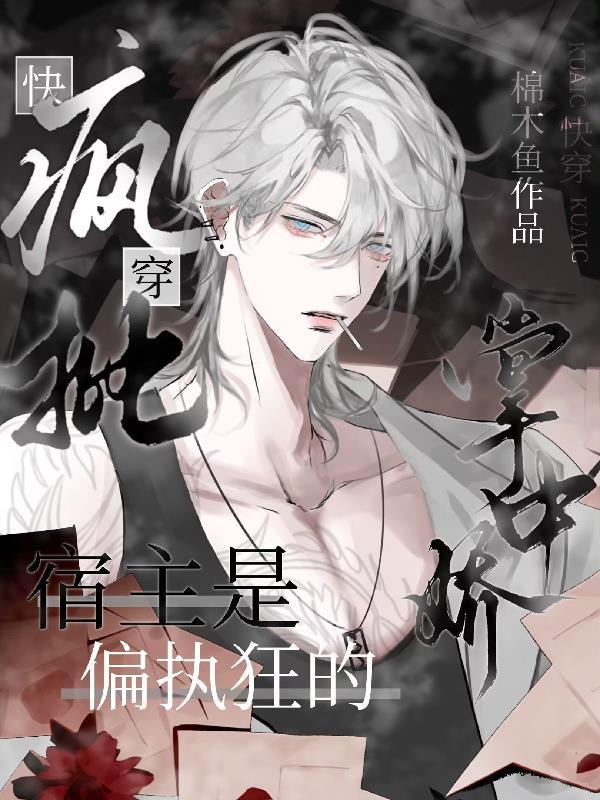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我当三界话疗师那些年 > 8星河入梦(第3页)
8星河入梦(第3页)
不过瞬息之间,暗沉的乌黑云层便已侵袭至三人身侧,雷鸣之声在耳畔远近震响。
冷风带起雁星河的黑发,掩去了他的眸光和神色,褚眠冬却在一霎亮起的电光里,看见了青年下颌处那抹晶亮的水迹。
“我不配啊。”
梦境之景是主宰者心境的映射,密布的阴云明明白白折射着雁星河的阴郁与绝望。
推倒了心中那栋由老阁主建起的扭曲高阁后,在从未体会过的解脱感里,他站在一片废墟之上,茫然四顾,无所适从。
而心中的另一个他,谴责着这个坠入迷茫、无力应对接踵而来事项的他,直至他近乎崩溃,下意识想起那些贬低之语,再次坠入自我怀疑的深渊。
“也许老家伙说得对……所有的美好都注定离我远去,而看清这事实却依旧无力反抗、只知道逃避的我,当真什么都……”配不上。
倏忽间,发顶处落下带着些许力度却依然称得上温柔的摩挲。
雁星河愣了愣,不自觉睁大了眼。
发丝摩擦的细微声响与掌心传导而来的柔和热意交织,自头顶绵延而下。
因思虑难全而一直隐隐作痛的心口似有所觉般重重一跳,有些兴奋地开始鼓噪,试探着燃起名为希冀的火光。
“哈……这样的我,却还在期待啊。”
雁星河知晓,这无关情爱与心动,而关乎一些更深层的存在。
他在期待一个人——谁都好——告诉他,他不差;告诉他,明云所言的爱和被爱真的存在,而他值得这些。
因为从未有谁曾这样告诉过他。
乏善可陈的前二十年里,明云是带领他看见门外有光的那个人。
而站在门口时,从未真正感受过光亮的雁星河犹豫了。
他忽而不敢直视站在光亮中的明云,也不敢将那些自卑与茫然向明云一一摊开,他已经拖累明云太多了。
他们已经太过熟悉,以至于他总是小心翼翼。
而褚眠冬与燕无辰则刚刚好。
并不熟悉、身处梦境,于是能够无所顾忌;
并非友人,于是能够以报酬两清,无甚心理负担;
由明云引导,又增一分可信。
理智这般分析,情绪却依旧难明。雁星河依然难以摆脱不配得感的纠缠,尖锐的叫嚣在脑海中穿插呼啸——
你可真是一滩靠吞吃他人光亮苟延残喘的黑泥,一个明云不够,还妄想着祸害拖累下一个。
你这些见不得光的算计,倘若叫面前的两个人知晓,也定会骂你一声“卑劣”罢?
等待两人开口的空隙里,他的犹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加剧,直至慢慢将他彻底压倒,心口渐渐被冰冷的黑沉潭水淹没,坠坠的冷。
也许只过了一瞬,又或许过了很久,他终于再也坚持不住,开口时,才发现嗓音业已嘶哑。
“不……当我什么都没说罢。这样的我如何配期待更多……”
这一次,打断他的是少女的温和嗓音。
“少阁主,我能称呼你为星河吗?”
这话语声并不大,却携着某种坚定的意味,穿透重重风雨之声,清晰地传入雁星河耳畔。
他应当是点了头。
“星河,你并不卑劣,也并不懦弱。”
湿凉的腕间传来温热的触感,是一双手,将他攥紧的指尖一一掰开、握在手心,弥散出丝丝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