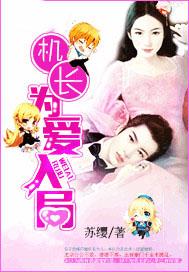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大理寺卿今天修罗场了吗 > 7080(第3页)
7080(第3页)
“你身为中书侍郎,陆氏倒台后,尚能独善其身,实属不易。”李珣语气带笑,却听不出温度,“今日中书一位,朕欲命你暂代,可有不愿?”
朝堂之上,一时哗然。
沈秉面色微变:“陛下,苍侍郎年方二十四,恐非朝仪所宜。”
左庶子亦上前奏言:“中书调政,非少年才俊可担。陛下若以其才而用之,可再观一二年,不妨从刑部、兵部中历练一程。”
李珣闻言不恼,只微抬袖角,似是在拂去案几上的微尘,语气慢条斯理,眼中寒意不显:
“诸位言之有理……可若论年资与才器,汉初萧何随高祖定天下时也不过三十,曹参守律令、张良谋帷幄,哪个不是年少得任?”
他指尖轻轻敲了敲玉案,道:“再往前,春秋时齐桓公任管仲为相,管仲之名,流芳百世,登朝之年也不过而立。”
“苍晏今年二十四,出身清正、学贯六经,文章、策论、筹略皆不下当年张良。”
语锋骤转,声色俱厉:“朕不问他年几岁,只问——此人,堪为我所用否?”
“苍晏虽年轻,然学问文章朝中谁不知?治政之才,昔日由陆氏压制,今得拨云见日,未尝不是天时。”
话锋至此,众臣俱默。
李珣转首,目光重新落在殿中那位立得极稳的年轻官员身上,语调忽然转轻,带着一丝意味不明的调侃:
“苍卿向来聪明,有胆有谋,也不负‘书阳’之名……但孤好奇的是,像你这般‘聪明人,可愿真心为孤所用?”
这句话,才是这场朝会真正的试刀之锋。
紫宸殿一时间鸦雀无声,连外头风吹铜铎的声音都显得格外清晰。
苍晏垂眸半息,忽而抬头,眼中一片清明,字字沉稳:
“臣不敢妄称忠心,但陛下之所求若是社稷长安、百姓无虞,臣愿献所学所能,供驱策一用。”
话虽未说“忠”,却进退得体,将自己置于“国政”而非“君恩”之下。
李珣唇边笑意加深,却听不出喜怒。他慢慢点头,语气却凉了一分:“你倒比陆长明还会说话。”
他微微垂下眸,语气轻柔却无懈可击:
“陛下既为天子,臣自当听命于天。”
李珣眸中光芒一闪,未言语,只轻轻笑了一声,长指捻过玉简,懒懒倚在座上。
“你啊……”他语气颇有玩味,“倒真是个读书人。”
“有点意思。”
他忽而抬手:“宣旨。”
“苍晏暂代中书令之职,三日后入直东阁,辅修政事。”
殿中群臣跪下应旨,苍晏也缓缓低头,一字不漏地叩谢:
“臣,领旨。”
李珣望着他颀长沉静的身姿,眸光微敛,低声自语:
“若你真能成朕手中之刀,最好;若不能……也罢,利器断人,自可弃之。”
朝散鼓响,百官退朝,殿外寒风初起。
苍晏负手缓步出殿,神色平淡至极,既不显喜,亦不现怒,宛若方才那个受命登相位的少年,并非他。
走廊尽头,有人快步赶上来,拱手一礼,语带笑意:
“恭喜苍大人,青云直上,从此百官之首,可要常开中书门了。”
此人是礼部侍郎陈羲,话说得极巧,语意又浅,既能当恭贺,也能作讥讽。
苍晏顿了一顿,回以一笑:
“陈大人说笑了,苍某不过暂代一职,还得仰仗各位前辈多提点才是。”
语气恭敬,姿态却毫不低微,一寸不多,一分不少。
不远处,有人冷笑插言:
“苍大人少年得志,果然不凡。听闻陆老病中前还念着你这位门生,怎的他前脚去了,你便顶了中书之位?两位先生教得好,门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