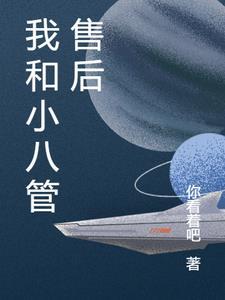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海水未蓝时 > 4050(第19页)
4050(第19页)
哪怕她真的是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被姑姑抱回来的孩子,哪怕她并非父母的亲生骨肉,可在日复一日的养育中,在她虽然矮小瘦弱但仍会帮妈妈搬东西的身影中,在她对着生日蜡烛虔诚许下“去大城市赚很多钱让爸妈不那么辛苦”的愿望里…在所有她倾尽一切去爱家人的单纯善良中,做父母的真的没有被打动哪怕一点点吗?
究竟,有没有把她当作真正的孩子来疼爱呢?
崔璨随手拉开桌子里的抽屉,妈妈也会买首饰,纯金的项链,吊坠是如今并不时兴的弥勒佛,依旧安安静静地躺在盒子里,金灿灿。
小的时候她很爱臭美,眼巴巴看着妈妈的金项链,好奇地问:“为什么买了不戴,要放在抽屉里?”
妈妈笑着摸摸她的头,把项链放回去,声音温柔:“妈都给你留着,你不是喜欢嘛,长大了给你戴。”
一晃快要二十年-
夜里崔璨被梦魇困住,翻来覆去都是她委屈地在问爸妈:“我也是你们的孩子啊,亲不亲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也会给你们养老,一直照顾你们的啊……”
“你们也是爱我的对吧?”
梦境再一转,变成了那个闷热难当的夏夜灵堂。她跪在堂前,夏天夜里,蚊虫在低瓦数灯泡周围乱飞。
她疲惫地席地而坐,在空无一人的地方难过地掉眼泪,对着两张遗像,声音轻得像呓语:“我不去南理了,就在宜川,反正我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好,也没有那么不喜欢这里…”
崔璨絮絮叨叨地说一大堆,最后也都只落脚在带着哭腔的恳求里:“你们能不能回来啊,别丢下我一个人。”
醒来是满头的汗,她大口喘着气,甩开身上沉重的被子,才发觉手脚一片冰凉。她呆坐了会儿,从梦里清醒过来,才起身下床。
客厅的灯关了,她记得睡前她特意留了一盏,又或者是她记错了。
崔璨凭记忆伸手开灯,却陡然听见低沉而带着睡意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怎么醒了?”
开关被按下的清脆声和她因惊讶害怕而发出的“啊”一同响起,是周序。
他亦睡眼惺忪,高大的身影笼住她的,崔璨惊魂未定,虚虚地伸手拍了拍他胳膊:“你吓死我了!”
周序拉她过来坐下,他今天开完会,才看到她发来的信息,等处理完工作,已经很晚了,怕她出事,又回家拿了趟崔璨之前给他的自家钥匙,轻手轻脚地进了门,没敢动弹什么,打开她卧室门发现她睡得正熟,又轻轻关上,自己窝在沙发上凑合着睡。
他抓住她的脚踝,把自己带来的药喷上,修长的手指轻轻按摩吸收,崔璨就势窝在他怀里,周序这才低头去看,发现她额头上细碎的湿发。
“睡的不好吗?”
她使劲汲取他怀里的温度,不紧不慢地答:“嗯,做好多梦,开心的不开心的,很杂乱。”
“要喝水吗?”
崔璨点点头,“我出来就是要找水喝来着。”
周序起身,将厨房的灯打开,去给她倒水,崔璨盯着他身影,眼神贪婪而珍重,像是盯着这个世界最后一个和她有关联的人。
他来得匆忙,也怕动作大了吵醒她,只脱了外套,身上那件质地精良的白衬衫被压得有些皱巴,想必是在沙发上不好舒展。
崔璨接过他手里的水杯,偏热的温度,让她紧绷且难过的胃有了暖意。
“关灯。”崔璨朝开关处努努嘴,拉着他回自己房间。
被窝已经全然没有了热度,崔璨整个人都被包裹在周序怀里,异常安稳。
两个人都没说话,又好像都没了睡意,过了会儿,周序开口叫她:“璨璨…”
崔璨被耳边声音震得心脏发麻,悄悄和他拉开了点儿距离,“怎么了?”
周序又把她揽了回来,两个人以更紧密的姿势贴在一起。
“我嘴笨,不会说话,但是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和她姓什么、从哪儿来、是谁的女儿、谁的姐姐都无关,他就只是喜欢她,纯粹而执着。
崔璨没有吭声,只是更紧地往他怀里缩了缩,额头抵着他的锁骨。周序也不要求她回应,宽厚的手掌放在她单薄的脊背上,带着令人安心的力量,一下,又一下,轻轻地、有节奏地拍抚着。
而后他感受到了湿润,崔璨吸吸鼻子,把眼泪使劲往他身上蹭,声音闷闷地传来,像是在对他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好像不应该这么大反应,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反倒让我减轻了一点心理负担。”
“但我只是讨厌被欺骗、讨厌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周序,你一定不要欺骗我。”
“嗯,不会。”周序收紧了手臂,下巴轻轻抵着她的发顶,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一丝犹豫,“不会。永远不会骗你。”-
崔璨照常上班,她暂时不太想思考这些事情,周序开车送她去学校,她在和他说了这周回他家之后下车。
倒是也没有那么忙,可她又需要用一些忙碌的事情把自己的情绪逼下去。
周序周四要去母校宜川一中一趟,之前申报的扩校计划得到应允,宜川政府也把地给批了下来,其实集团有专门的负责人对接这件事,但周序表示自己还是专门走一趟,以示重视。
校方对华建集团的支持表示了高度赞赏和感谢,洽谈过后是熟悉的饭局,助理预定了宜川大酒店的包厢,话题一开始只是这一扩楼的这一项目,酒过三巡之后,饭桌上曾教过周序的老师就开始忆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