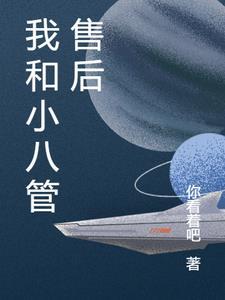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海水未蓝时 > 4050(第18页)
4050(第18页)
“我一开始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周序,你明白吗,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人…”
“其实他们可以直接告诉我的,说我是被捡来的,说我必须乖乖听话他们才会继续养我,没问题的,我都会接受,我就是觉得,好讽刺啊…”
她泣不成声,肩膀微微颤抖,“我一直都渴望远方和资逸,拼了命地想挣脱那些所谓的亲情和家庭的束缚,甚至当初…爸妈走后,我也不是那么情愿回来照看崔木宸,我心里不是没有怨,我还总觉得是他们用责任捆住了我…”
她的眼泪越流越多,周序的手轻轻擦过,又有新的泪水落下来。
“可是怎么会这样啊,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真相,这是我的责任,我欠的债,我必须要还的,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退路…我反而…反而会更任命地去做啊!”
“周序,”她抬起泪眼朦胧的脸,无助地望着他,问出了那个最根本的、撕裂她所有身份认同的问题,“可是…我是谁啊?”
她是生来就被遗弃的女婴,是幼年不被重视的女童,是拼命读书向往更大更远世界的女学生,是被勒令要懂事要谦让要担起责任的姐姐…可她唯独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到底是谁啊,宇宙论和本体论无法告诉她答案,血缘关系和亲疏远近也一并失效,她是这偌大世界里不知来处亦不知归途的盲流。
崔璨哭累了,紧绷的神经在温暖的怀抱里陡然松懈,周序被难过的情绪攫住,耳边长久而反复地回荡着她陷入昏睡前,那句轻飘飘却又重逾千斤的呓语:“原来…我真的是浮萍啊。”-
成人世界里没有那么多可以肆意挥霍或是可以暂停的时间,第二天一早,崔璨依旧在闹钟响起的第一瞬就摁掉,她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换衣服、洗漱、背包、出门。
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动作流畅,却毫无生气。
她还有课要上,还有学生要教,“我是谁”这个问题被搁置,她迫切地需要用接连不断的事情堵上自己胡思乱想快要爆炸的脑袋。
起码现在,双脚稳稳地站在地上,她就仍需要向前。
虽然有些疼。
“昨天摔的?”周序蹲在她面前,温柔地捏着她的脚腕,眼神多有怜惜,语气又有点无奈:“先带你去看医生行不行?”
崔璨摇摇头,“不是很疼,再说吧。”
刚开学的任务量并不大,上午只有一节课需要上,中午有老师喊她一起去食堂吃午饭,崔璨应了。
学生在一层吃饭,许是刚开学,人流量还挺大,她们走上二楼的教师食堂,随意找了个位置便去打饭。
“小崔老师你吃这么点儿啊?”同行的女老师看到崔璨面前那么一点饭,不由得诧异道:“怎么了?咱们饭堂的菜还可以,要是不喜欢,下午咱俩点外卖,我知道新开那家轻食沙拉不错。”
“没事,是我不太饿。”
她的面前,只有寡淡的两道菜,清炒西兰花,几片冬瓜,—半个拳头大小的米饭。
这个毛病很久了,她只要心情不好,食欲就会变得非常低,硬要吃下去的话,搞不好会吐。
身体在用另一种方式宣誓着主权,她也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对抗-
第二天下班的时候,崔璨给周序发了微信,说自己今晚不回他家了。
他没回复,可能是在忙。崔璨收拾好东□□自走出校门。
两晚没回来而已,家里却显然冷清许多,崔璨放下东西,换好鞋子,径直走向那个已经很久没被打开的房间。
陈旧的味道扑面而来。
崔璨四下观望,父母的房间是最大的那间卧室,可如今已经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曾经的床上已经没有床单被子等一系列床上用品,木头打好的床板之上是有些凌乱的杂物,角落的桌子上摆着两张黑白照片,崔璨走到飘窗处缓缓坐下,伸伸双腿,便触到了床脚。
房间里一同漂浮着令人窒息的沉默微粒,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了。
过了会儿,崔璨起身,走两步到床边,伸手翻了翻床上的东西。
父母学历都不高,几本厚厚的像书本一样的东西,是这些年的账本,有门店的,也有生活中的。
崔璨耐着心找,从最上面找到最下面,找到一本年月久远的,是墨绿色的封皮,纸张有些脆,被水沾湿过,可上面字迹依旧清晰。
她小心翼翼地翻动,仔细辨认上面的字迹,奈何经年累月,除了最开始几年的奶粉钱,都只是一些其他的生活开支。
父母都不善言辞,关于她的痕迹,就连账本上的记载也少得可怜。
没有任何文字、语句,或是照片、影像,可以帮她回忆起她的来处,她在这里停留,而后被捡起,扎根、成长、远走,又因命运的捉弄而回来。
一切都戏剧得像是影视剧里才会出现的套路。
崔璨扯了扯嘴角,发出一声短促而自嘲的轻笑。她将账本和其他杂物,按照原样,一件件放回原位。在挪动整理的过程中,她突然明白了自己在执着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简单到近乎卑微。
她终其所有,都只是在找寻一件事。
——她曾经被爱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