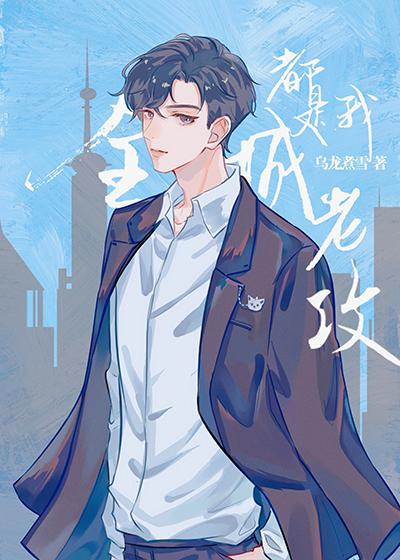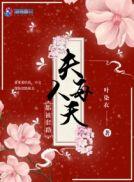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朕的一天 > 90100(第4页)
90100(第4页)
她迫不及待地问讷讷,“是什么时候的
事情呀?都还好么?”
讷讷笑着答,“这么高兴?是下午的事情,母女平安。他们来报信的时候,你不在家。”
讷讷不忘叮嘱她,“过会子到人家家里去,可不兴再一口一个孙大大了。”
她挽着讷讷的臂弯,头靠在讷讷的肩头,亲昵地说,“我知道啦!”
讷讷回握住她的手,不免感叹,“那位三爷,是平辈儿里成婚最晚的。当时他阿玛不肯松口,他非卿不娶。儿子和老子斗法,最后还是爷爷出来说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他那么多。他阿玛才没多说什么。”
连朝当时也听过这位三哥哥的“光辉事迹”,和他老子斗得不可开交。绝食啦,写绝笔信啦,私奔啦,关祠堂啦,寻死觅活的事都让他干了一遍。不过他也聪明,做事不做绝。绝食给自己留块点心,私奔给家里留张纸条儿,绝笔信是放在家里人一眼就能看得见的地方的,上吊是让小厮在外面掐着点儿,凳子一踢外头小厮就扯着嗓子喊人。
总之,想死是真的,死到临头千方百计想活命,也是真的。
她和敬佑一度很佩服那位哥哥,敬佑说果然孙子最像爷爷,这位三哥哥惊天动地地追求爱情,当真是他们这一辈儿里的楷模。敬佑甚至还摩拳擦掌,想着什么时候和这位三哥哥切磋一下,也学点气老子的技巧。
好在孙大大纵容他,老三的阿玛在老三面前是老子,在孙大大面前还是小子。孙大大有样学样,把老三阿玛骂了一顿,老三总算如愿以偿,热热闹闹地把心上人娶进家门,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他们当时都以为,这位三嫂不是个一般的人。
一辈里的人都传,她能让老三对她这么死心塌地,想来一定有很多手段。有人说她靠秘药将老三吃得死死的,有人怀疑她身世不清白,有人怀疑她是仇人家的孩子,处心积虑接近老三就是为了报仇。传得玄乎其玄,每一个听起来,似乎都有那么点道理和动机。
可真见了面,相处之后,才发现她并没有传闻中那么不堪,甚至也没有什么手段。她与寻常女子一样,温柔,平和,待人接物,周详体贴。
她于是很好奇地问讷讷,“当年为什么那样子闹呀?两情相悦,有什么不好?再说三嫂嫂,也与传闻的,压根儿不一样呀。”
讷讷无奈地看了她一眼,本不欲回答她,不知想到什么,还是低声说,“哪里有那么神乎其神。不过是问生辰八字的时候,那方士断言,她无宜男之相罢了。”
连朝听得笑出声,直摇头。
不计较那些前尘往事,她说,“无论如何,孙大大应该很高兴。”
讷讷说那是自然,“年前孙大大来辞路,后来下了场雪,不能下床,家里都怕他过不了年关,没想到他熬过去了。我私心里想着,老人家心里应该还是盼着重孙。”
连朝附和,“如今等到新生,说不准能振奋精神。”
讷讷不再答话,只是笑了笑。
她们母女两个下车,早有人在门口等候,笑盈盈地迎她们进屋说话。
一路过了二门,看见满地红纸屑,便知道已经放过炮仗了。那孙三爷穿着簇新的银红袍子,正站在廊下和客人说话,远远瞧见她们,笑着招呼,“婶婶和妹妹来啦?额捏在里头,婶婶和妹妹请吧!”
诺夫人笑道,“新做了阿玛,恭喜,恭喜。”
孙三爷赧然地摸了摸后脑勺,笑着叹了口气,“承婶婶的贺!我高兴……就是辛苦她。以前不知道妇人生孩子的艰难,下午经历一回,我在外头看着都揪心……”
诺夫人问,“有这份体贴的心,便比什么都要强。”
又说,“今儿家里客人多吧?”
孙三爷说,“下午生了之后,就报喜信给叔伯婶婶们知道。我想着她已经很累,实在没必要一下子请那么多客人,让她先休息好是正理。哼,”
他冷笑一声,往前边望了望,“有人之前满嘴不在意,袖手不管,真做了玛法,恨不得普天同庆,恨不得来一个客人放一轮爆竹,把屋顶都炸翻了他高兴呢!”
这话说得诺夫人和连朝都笑了,诺夫人劝他,“儿子和老子之间,哪里有什么世仇?”
孙三爷已经亲自将帘子打起来,“外头冷,婶婶和妹妹进去说话吧。”
诺夫人便领着连朝进屋去。屋里暖和,孙夫人正嘱咐几个嬷嬷一些事宜,边上围坐着一些亲戚太太,见诺夫人来了,起身相迎,问过好,又寒暄了几句连朝,无非是“出落得标致了”,“可有相看人家”云云。
孙夫人携诺夫人坐下,说了会子话,保母便将孩子抱过来了。几个妇人围在一起,看着襁褓中的小孩子。
这是连朝第一次看见新出生的小孩,她好奇地站在讷讷身边,微微弯腰去看。有些泛红的一张脸,还没有巴掌大,眼睛闭成一条线,五官皱巴巴地挤在一起。红润的嘴唇,柔软的、乌黑的头发,握成拳的手,还有香甜的呼吸,这种种无不昭示着众人,这是一个崭新的生命。
那样美好,那样小。
充满着无穷的可能与希望。
众人看了一回,保母便将孩子抱下去了。有人问,“定了小名儿没有?”
孙夫人说定了,“小名叫做喜格。”
诺夫人附和,“正月初二日生的,还在年节里,一家人和美团圆,就是最可喜可贺的事情了。”
孙夫人笑道,“正是这样。下午老爷子精神也好了很多,这几天原本没进什么油水,破天荒地忽然说要想吃些米粥。自打这孩子一出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就像心里头出了太阳一样——我不太会说话,让你们见笑了。”
诺夫人说,“那真是件好事。刚才我打外头进来,和三爷说了几句话,做了阿玛的人,显见得更踏实,更稳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