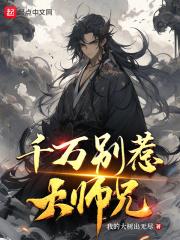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赋彩[公路] > 4050(第24页)
4050(第24页)
“所以我们,算是分手了吗?”周亓谚把手揣在口袋里,隐藏指骨的青白。
宁玛笑了笑:“半年而已,我们就把这当做一次艳遇吧。”
她说完之后,转身朝前走去,连一句“再见”也没有留。
宁玛没敢回头,排队、放行李、递证件,一气呵成。她在夹在高大的外国人之间,他们的香水味复杂又浓郁。
其中有一丝微弱到极致的柠檬调,宁玛终于忍不住“唰”地回头期待视线里那抹熟悉,但远处再也没有周亓谚的身影。
“女士,您已经升舱,可以走另一边的快捷通道哦。”有人将她唤回来。
“什么?”宁玛抓紧行李箱的提手,紧张询问,慢慢才理解航司人员的话。
并不是什么免费升舱大礼包砸到了她头上,这当然是周亓谚送她的,最后一个礼物。
宁玛被带去贵宾休息室,服务者轻声细语,端上果盘点心,询问要什么饮品,温度是否舒适。
忽然,她看见这位黑头发的华人女士愣愣坐在那儿,眼睛里滚下一片泪。
服务员吓了一跳,为自己的考核而担忧,于是赶紧过去安慰贵宾。
“女士,一切都会过去的,您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她给宁玛递上纸巾,又蹲在她膝盖边安慰。
“对啊,回家。可是……他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回家。”宁玛把自己的脸捂在纸巾里。
在周亓谚送她的最后一片空间里,宁玛痛痛快快大哭着,她好像忘记了学习过的所有,能开解心情的佛家偈语,眼泪不停地滚落,纸巾一张叠一张,像是在心里为这场“艳遇”垒出一座玛尼塔。
第50章方解石白牦牛
水土不服姗姗来迟,宁玛在高空中陷入反覆的低烧,蜷缩在机舱座椅里,好像是灵魂在进行一次自我的剥离。
她迷迷糊糊睡到回国,落地首都机场的时候是大年初三。这是一个不前不后的日子,机场里冷冷清清。
宁玛站在机场的电子牌下,地名闪烁变化,她突然看见了“成都”。一瞬间,记忆里的方言音调,混合着朦胧湿气,辛辣地钻入脑海。
于是那一刻,她突然决定先不回敦煌,而是转道成都。
听说在东北,生病的人都想吃口水果罐头,这大概与童年记忆有关。对宁玛来说,她此刻很想吃一口藏餐。
宁玛从双流机场坐地铁,按照手机导航,找到武侯祠旁的一家藏餐厅。出站的时候,灯火璀璨,这里没有大到让人睁不开眼的寒风,人们穿着各色大衣和羽绒服,在街头熙熙攘攘。
她推开餐厅的门,穿着藏装的服务员口喊“扎西德勒”,宁玛抬手回礼,然后一个人落座。
虽然之前在成都三四年,但这家据说很正宗的藏餐厅,她却从没来过。一方面是当时的她,有意想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和语言。另一方面,是她真的囊中羞涩,消费不起。
如今回头一看,宁玛才发现,她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
给她上菜的也是一个女人,她先给宁玛拎来一壶热奶茶,接着又端上一份玛森糕,最后在上主菜牛肉盖被的时候,她终于没忍住,试探地问:“你是……冷措寺的宁玛吗?”
奶茶顺着宁玛的嘴角洇出来,她赶紧拿纸巾盖住,震惊地看向服务员。
她是典型藏族女性的模样,骨相比宁玛有说服力得多,她对着宁玛露齿笑,睫毛漆黑而羞涩。
“我是拉姆。”
“白牦牛?”
两个姑娘异口同声,然后一齐笑起来。
“你的样子没什么变化,我一下就能认出来。”拉姆说。
宁玛笑了笑,问:“你怎么会来成都?不会舍不得白牦牛吗?”
拉姆和宁玛是小学同学,拉姆家在去往冷措寺的路上,两人常一起上下学。
拉姆十岁那年,家里诞生了一只纯白的牦牛,小女孩宝贝得不行,每天喂食梳毛。甚至宁玛也沾过这头白牦牛的光——和它分着喝牦牛奶。
小学毕业的时候,宁玛继续去镇里念初中,拉姆自己则放弃了学业,因为初中比小学更远,需要住在学校,她舍不得白牦牛。
但宁玛知道,这不是拉姆不再上学的全部原因。
“白牦牛现在交给我哥哥了。”拉姆说,“它陪游客拍照,赚得比我多。”
“拉姆,你在和客人说什么?”一个男人掀开后厨的帘子走出来,用藏语嘟囔着。
“贡布,这是宁玛,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拉姆回头介绍。
宁玛也点头用藏语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