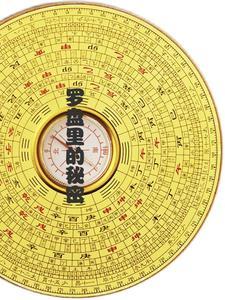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误慕高枝 > 6070(第30页)
6070(第30页)
周玉霖无计可施,府上围得跟铁通一般,他只能发怒砸东西。
徐氏过去时,房中已没落脚的地了,她踩上一只瓶罐,险些滑了一跤。
“夫人小心。”
身旁的嬷嬷扶住她。
她推开下人,忿忿上前,“忤逆不孝的东西,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你跟我撂什么脸子?我是为你好,蓉儿知书达理,哪里比不上一个市井女?”
从前都是她心太软,儿子稍微作求她就放人出去,没想到心越纵越野,被一个乡野女子带坏了。
这回她不能再容他胡闹,她娘家的侄女,他不娶也得娶!等娶了妻,有了家世,就好好地去读书,万不可这般吊儿郎当。
“娘,你别逼我!”周玉霖坐在地上,将酒盏一砸,似是喝醉了,开始说些胡话,“我从小到大都被你们逼着我干不喜欢干的事,我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都要听你们的,你们逼我读书,逼我作文章,逼我娶我不喜欢的女子。我有时甚至想,我若不是周家的少爷就好了。”
徐氏被她说得心揪成一团,眼眶红热,朝他扬起巴掌,手却悬在空中颤抖,终归是不舍,只能扇在自己脸上。
“娘,你这是做什么!”周玉霖拂落她的手。
徐氏推开他,冷笑:“你不是翅膀硬了,不想认我了吗?”
周玉霖一时无言。
徐氏踢开脚下的东西,继续道:“我的儿,人各有命,你从我肚子里出来,你就是周家的少爷!你小时候,我们一家还在渝州,你才三岁,浑身起疹子发高热,碰巧隔壁也有一户人家的小儿跟你一样的病症,他们家没钱,孩子没挨过三天就去了。我和你爹重金求医,银子如流水一般花出去,这才将你从鬼门关抢了回来,你若是不生在周家,你哪还有命活到今天!”
周玉霖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整个人像架在火上烤。
他没脸反驳娘的话。
可他也是真心喜欢苹儿,他是真的想娶她。
他曾经天真地以为他只要一闹,爹娘就会顺着他,他只要多求求爹娘,爹娘和姐姐们就会接受苹儿。
如今他知道的,他的话、他固执的坚持,在爹娘面前不值一提。
他的一辈子,早已被安排好了,只要他还姓周,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得了!
徐氏看他有所动容,俯下身劝他,“那女子我着人查过了,虽是奴籍出身,如今也已放良,能做起大夫,心地想必是善良的,也难怪你喜欢。你若实在放不下,等你娶了蓉儿,就抬她进门做个良妾,也不算薄待了她。”
“苹儿她不做妾!”
周玉霖声色毅然。
她知晓苹儿的心性,做妾无异是辱她。
徐氏火气上来了,指着他:“好好好,那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爹在回来的路上了,等他一回来,你与蓉儿就交换庚帖,把婚事办了,我们一家搬去扬州。你别想着逃跑,我要是能让你院里的一只苍蝇飞出去,我就不是你娘!”
姜芾与苹儿两人在打理布置新医馆,兰殷礼也派了人过来帮忙。
万事俱备,只差一块牌匾。
她还不知医馆的名字取什么,新的医馆,她必然要取一个自己的名字。
想来想去,在纸上写下三个字——念安堂。
念安,希望每一位患者来到这里回去,都能早日痊愈,平平安安。
她刚想托人去找专门为牌匾提字之人,那人还没出去,街上突然闹哄哄的。
“官兵下山了!官兵下山了!抓了几囚车山匪,大伙快去看!”
人群瞬时往那一处涌。
他们上山也有五六日了,姜芾闲下来时,也会时常想到凌晏池的伤,他就算身强力壮,也不是铁打的身子骨,擒贼必定凶险,也不知他的伤怎么样。
她立时关了医馆,也挤了过去看热闹。
可城门水泄不通,她竟没看到他人。
夜色已晚,她买了些菜独自回家,走到家门,已有人在她门前候着了。
凌晏池换了一身干净常服,身形高挑清瘦,只是眉眼有些疲乏。
“你怎么来我家了?”姜芾边说着,边打量他身上可有添新伤。
“我知道你担心我。”凌晏池在她面前转了一圈,笑了笑,“没有再添新伤。”
姜芾睨他一眼,没好气,“谁担心你了,我是被你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