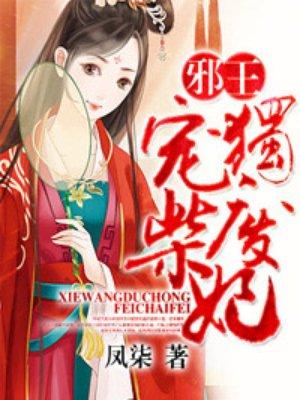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横刀夺取 > 6070(第7页)
6070(第7页)
陈则自己打开了电视,又放上回的《无耻之徒》。
夜里凑合睡沙发,没进卧室,电视放到凌晨两点多。陈则侧躺睡着了,贺云西捡了条毯子过来,坐沙发的另一角,默然盯了几分钟剧,中间侧头望望,确认他真的睡熟了,抓起遥控器调小音量,等了一刻钟才关上电视。
早上睁眼就九点多了,睡过了头。
贺云西还守在边上,陈则刚翻身,这位手撑在长腿上,正疲惫地揉着眉心。看起来像是一夜都坐那儿,没离开过。
也可能是起得比较早,醒来就坐着在等了。
扯扯身上的毛毯和被子,陈则压根不清楚这俩东西是哪个时候有的,翻个身,看到人一滞。
歇了一晚,昨儿的情绪已然压下去了,不讲难听的话了。
看了看贺云西,陈则先张口,太阳穴紧绷,有些痛:“几点了?”
贺云西回:“不到九点半。”
“你不上班?”
“还早,下午过去。”
起来,洗漱收拾,两个人先后进浴室,并肩站镜子前刷牙。陈则动作快,刷完了拧开水龙头洗脸,大冷天仿若感受不到凉水的冰彻刺骨,掬一捧水就往脸上招呼。
贺云西瞧见了,没说什么,掰水龙头开关朝向热水那边。
房子里早换成了零冷水,一开就有热水。陈则感受到了,热水淋到手心,他缓慢恢复知觉一样,顿了顿,整个人行动都慢了半拍,可紧接着当作无事,继续洗脸,揉搓两把就找毛巾胡乱擦干。
对于昨晚的事,最后没个解释,更不需要解释。
陈则不想啰嗦,贺云西不在乎,只是今早对方再跟着忙前跑后,陈则没话了,什么都没再说过。
元宵一过,大大小小的工地都开始复工了,孙水华徐工他们回来了,同样也听说了陈家的事。
曾光友不出意外失约了,老东西带外孙乐不思蜀,完全将年后的计划抛下,表示现在走不开,他女儿晋升了,儿女家的孩子都没人带,他老婆到儿子家带娃了,他得留在庆成市帮他女儿看一阵子孩子,最早下个月回,有问题电话里应该能解决。
大邹到医院照顾邹叔了,短期内也不来,这种时候还管什么工作,亲爹都快没了,大邹更好不到哪里。
孙水华和徐工有店里的钥匙,到了不等陈则,已经开店接生意了。
陈则和大邹的情况,他们都知道了,年前一贯比较刺头,不乐意听陈则指挥的孙水华规矩老实起来,不老是甩脸子,或是对着干添堵了。
店里大部分活都由孙水华和徐工接手,他们比大邹省心,双双老江湖,本就是曾光友的左膀右臂,什么都会做,什么都能做。
徐工第一天就拉了俩工地的合作单,孙水华更是靠谱,一改往常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德行,店里来客了基本是他在接待,需要出工亦是他背上工具箱出门干。实在是干不了的,才会找陈则,让陈则做。
知晓贺云西是陈则朋友,孙水华他们只当他是好兄弟哥们那种,避开陈则,徐工还找贺云西问了问,看陈则的状态明显不对劲,担心会出事。
贺云西说:“没事,别太担心。”
孙水华叹气晃头,别人活了大半辈子都不一定能遇上的几大难关,搁陈则身上,二十来岁就全经历了个遍,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世事无常啊,难说。
大邹不来店里,但工资还是照发,全店就这一个领固定工资的,虽然过年放假半个多月,但工资还是一分不少打到了卡上,十分准时,一毛不少。
大邹惊蛰当天回店打了一晃,来退工资,外加辞工。
不干了,干脆早些离职,避免耽误陈则再请人。
陈则没准,可双方又不是真的雇佣关系,本身连正式的劳动合同都没签一份,一个草台班子,学徒哪会签这个,所以大邹想走,陈则阻止不了。
“邹叔知不知道,他同意了,让你来的?”
“不是,他不知道,你别告诉他。”
陈则脸色难看:“说走就走,这么能耐有底气,行啊,有本事。清楚你这份工作怎么来的吗?你有什么资格?”
“我没有。”大邹说,任凭讽刺,半个字不反驳,冷静看着他,仅仅平和讲事实,“我爸要走了,我想多陪陪他,不想干了,难道不可以么?”
“不可以,你想休多久就休,辞工不行。你非要辞职也行,找邹叔来找我说,不然免谈。”
“他来不了。”
“那是你该考虑的问题,我管不着。”
大邹嘴皮子上下碰碰,喉结动动:“老大,你别逼我了,成吗?”
陈则有些不依不饶:“我逼你?”
“我只是来跟你说一声,本来我不想来的,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不需要,行不行,放过我吧。”
![流放后嫁给失忆将军[重生]](/img/15325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