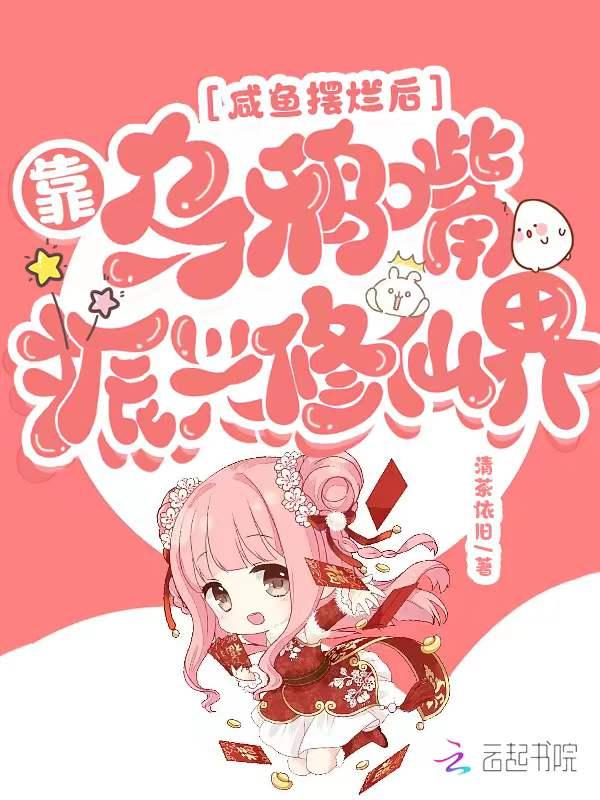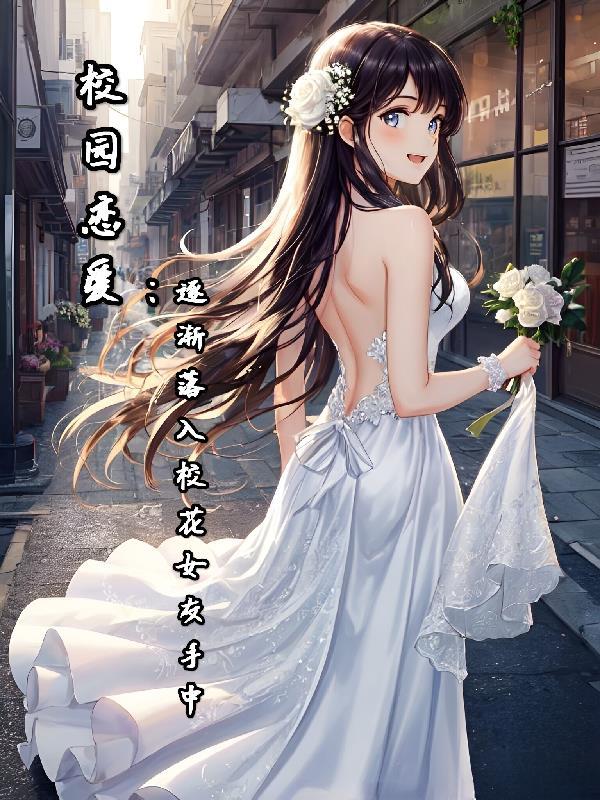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风前絮 > 宫斗过敏奇缘(第3页)
宫斗过敏奇缘(第3页)
原来,她体质特殊,自小不能盖丝绵制成的被褥,在陶府时,墨香也小心叮嘱,一定叫人换了蚕丝软被,否则不出片刻便要鼽嚏。
此时,她吸着鼻子,喉咙耳朵痒得实在有些难耐,认定这被子定是丝绵制成,索性不管不顾地翻开,下床来抖擞精神。此次实在痒得厉害,不仅鼻子痒,喉咙痒,耳朵痒,就连手腕和臂肘都痒了起来。
她挽起袖管看,见自己手腕处红了一大片,烛光下细细看去,像皮肤下身处点点滴滴的紫痧,看起来有些渗人。
她顿觉有异,连忙点起更多的烛火,凑到铜镜前去看,见自己从脖颈到胸前都红了一大片,指甲抓过处,皆是血红紫癜,小小的,密密麻麻,和手腕处别无二致。
凤仪殿众人已经睡了,她心里紧张起来,觉得此事耽误不得,慌忙将守夜的荷青叫醒。这情状吓了荷青一跳,捂嘴小声道:“二小姐,你。。。你的脸。。。。。。”
她连左脸亦开始有些发痒,静堂知道千万不可触碰,否则这紫癜就要蔓延得全身都是。
“别碰我,”她离荷青远远的,嘘声道:“快去烧热水,我要沐浴。”
现在已是三更半夜,何处去找热水。荷青没办法,只能把家里带来的暖碳尽数取出来,小壶小壶的烧。
静堂在一旁痒得跳脚,荷青急道:“二小姐,找个太医来看看吧。”
她虽是浑身难受,嘴上却说:“开什么玩笑,这样的事传出去,凤仪殿还能清净吗?不管了,有多少用多少,烧好了就拿来,越烫越好。”
荷青闻言只能低头去扇那炭盆,半晌,递来一盆滚烫的水,静堂不管不顾,把毛巾放进去烫开,热气滚滚地拿出来,放凉了片刻就朝自己的脸擦去。
温度烫红了半张脸,她细细看去,却没再起那些红疹,又迅速把手重新伸到水中,一次次取出滚烫的毛巾擦拭自己的身体。
“二小姐,”荷青在暖阁里蹲着扇炭盆,说道:“我记得你小时候是不是患过这样的病?”
“这不是病,”她被烫得嘶嘶喘气,却仍旧不停下手上的动作,“是以前被席虫咬了,浑身长这样的包。”
荷青顺着她的话回忆起来。
静堂道:“我就十多岁那年犯过一次,我哥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凉席,也没烫洗过就送来给我用,当时不懂,直到满腿都被抓烂了才去请大夫。”
荷青又从来一盆新的滚水,说道:“那就应该是了,如果是病,怎么就犯过一次呢?”
滚水走过一遍,她已觉得好了许多,静堂喘着气,小声吩咐:“这件事不许告诉姐姐。”
荷青取来治烫伤的药膏与她涂上,又与她服下六神丸,发愁道:“这样的事怎么瞒得住,脖颈了红了好大一片。”
又转头看看被褥,自言自语:“不应该啊,咱们宫里的东西都是清洗过的,被褥都是蚕丝的,怎么会烧成这样?”
静堂把毛巾泄气似的往盆里一丢,双手杵着盆沿:“我问你,皇后娘娘究竟什么病?”
“说是肺病,具体是什么,太医倒也说不好,只是每年都要犯上几次,二小姐没见过,皇后娘娘咳得厉害,有时就像窒息一样。”
“是痨病吗?”
“那倒不是,肺痨早就传染了。之前娘娘病时,大小姐还去侍过疾呢。”
静堂道:“我也时常起风疹,严重时也会喘不过气。荷青,你还记得去岁用错了被子,起风疹的时候恰逢高热,庄大夫用银针替我放血的那一次吗?”
荷青想起来,应道:“对对对,我记得,当时二小姐也是窒息的模样。”
她闭目叹气,重新去看自己手上的斑点。此刻已经不痒了,颜色却仿佛更深,她把袖子放下遮好,说道:“这床今晚是不能睡了,明日用热醋洒一洒吧。”
“是。”
她没说什么,转身出去到贵妃椅上躺了半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