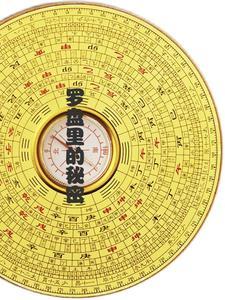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被饲养的金丝万人迷[快穿] > 第114章 朋友妻不客气(第1页)
第114章 朋友妻不客气(第1页)
第一次就是三天,要承受的还是s级Alpha的易感期,和月侵衣最开始想的一样,他的意识多是浮浮沉沉,无从靠岸的小舟般,在水面上持续不断被挑起,船舱里遍地是涌进的海水。
残缺腺体中大部分信息素都无法长久保存,冷薄荷是,依兰香也是,没一会就散得只剩一点,这一点在身处易感期的Alpha看来几近没有。
不是他的问题,他咬得很深,恨不得将里面都填满。
那就是Omega的原因,他的Omega不喜欢他,所以不愿意留下他的信息素。
暂时失去清醒的Alpha无法理解什么是腺体残缺,也不想理解,动物圈占地盘般,只想把Omega浇透,全身每一处都是自己的信息素,以此直白宣誓主权,震慑所有企图靠近的外来者。
身下的人瓷白的皮肤上模模糊糊浮上层淡粉,眼睫一簇簇连成一排小三角,是润透了的乌浓。
鸦羽般长睫下时而凝出几滴圆润水珠,有的是线串般滚落,有的则要掉不掉地缀在眼尾,在无法抑制的轻颤中滚落,没入鬓角。
他微偏过头,湿白的侧脸陷进柔软的枕面,时急时慢的呼吸中,颈间线条也起伏连绵,流畅曲美,皮肤沁着那层淋漓水光忽闪,近乎透明下细小血管时隐时现。
因为被迫打开,Omega腺体中涌出了许多信息素,但在漫天依兰香里依旧不够看。
信息素是Alpha招摇讨好Omega的手段,也是Alpha欲念的外化,有时连Alpha自己都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信息素,只能藏起窃喜,面上无奈地任由自己信息素缠上Omega。
像无形的尾巴,信息素总将Alpha藏不住的心事摇得欢快。
依兰香落在Omega淡红眼皮上,又亲亲密密地缠上他指尖,无力蜷起的细白手指下是被拽扯出大片褶皱的床单,他早就分不清自己是抓握住了还是没抓握住。
模糊余光中,元旭紧盯着他,面上神情不明,像是清醒了又像是还没有。
如果清醒了,月侵衣就要让他先停一停,而他会听话,但他每次清醒的时间太过短暂,其中间隔的时间也越拉越长,似乎是不愿意清醒。
月侵衣努力辨别他眼中情绪,想以此判断现在是哪个他,但现实中的处境让他思绪很乱,怎么也串联不起来。
在他忍不住想含住自己指骨咬的时候,整个人忽然被掀了过去,元旭再次将自己埋进去,不满地凑到他颈间腺体舔吻。
小而瑟缩的腺体吝啬地只肯给他一点信息素,只有刚才被他咬进去的时候给得多了点。
又不肯帮他含着,里面属于他的信息素越来越淡,明明才没过多久。
临时标记对于残缺的腺体来说几乎没有一点用,不能宣誓主权,也不能赶走外来者。
患得患失的Alpha在Omega后颈微鼓起处留了一串湿漉漉的吻,尖而硬的齿端几次都在上面轻划过,蠢蠢欲动。
那里不能给人随便碰,更别说咬了,元旭行为性质极其恶劣,月侵衣抬手覆上,不许他再继续,他却无法理解其中拒绝的意味般,含咬住那几根手指。
湿热触感伴随着磨痒。
等手躲开了,他又继续低头专心咬那个小鼓包。
无知无觉,看不懂拒绝,不要脸但爽。
在他齿间若有若无的胁迫下,微鼓腺体颤巍着递出一丝又一丝氤氲水汽的茶香。
绿茶信息素很柔和,但元旭却像是被刺激到了般,越来越激动,几乎要直接撞开那道小门。
但不行,那扇门还没给谁开过,太小了,他又太大了,他再怎么意识不清醒也不敢乱用劲,只能一点点凿,等浇透了,成熟了,门才会开。
上瘾般,元旭沉溺于埋在月侵衣颈间咬咬舔舔,不放过每一丝信息素,等终于舔够了,舔不够,只是他不满足于舔咬了,元旭拨开月侵衣唇边粘黏的发丝,细心地帮他勾回耳后,目光在薄红侧脸上停了又停,终于没忍住极为缠人地蹭了一下。
“给我咬吗?”
他蹭了一下,又一下,很多下。
月侵衣只躲了一次,就被他报复般缠得更紧。
他不知道什么叫装聋作哑,也不知道身下人不想理他,得不到回应他就一直问:“咬吗?给我,可以吗?”
月侵衣摸索出来一点他的性格,知道他最喜欢断章取义,只听想听的,回答时只简单一个字:“不。”
回应他的是Alpha更加激动的动作,以及颈间的再次被咬破的细微疼痛。
进化了,不再是断章取义了,直接指鹿为马,Alpha根本就没打算得到他的同意,只想听他和自己说话,一个字也行,容易满足又不容易满足。
越来越深,依兰香再次覆盖在腺体上。
可能他也知道自己太贪心,这次他没有失控地往更深处咬,只比商行川之前留的深了一点中的一点就停了。
善妒爱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