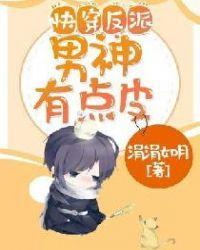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怪盗一缕春 > 第 15 章(第1页)
第 15 章(第1页)
“当当当——”
深夜,王府府邸的门环撞了三下。
“吱呀——”朱红大门开了一条小缝,看门婆子看见一个年二十七八的面生姑娘,想要驱赶。
话未出口,就见姑娘掏出一块刻着“巡检”字样的木牌,往眼前一放,随即插回腰间。
连翘面带风霜,声音沉稳,“开封府办案,事关王大人遇害及小姐清誉,烦请通禀,速见小姐。耽误了正事,你担待不起。”她语气不容置疑。
婆子被那眼神和腰牌唬住,又听事关老爷和小姐,不敢怠慢,慌忙进去通报。
连翘平静地等待着,想起昨夜。
王家墙外,一缕春转着圈圈,一筹莫展,“现在想要洗清罪名,必须找到王小姐。可我这双眼睛,瞎子才认不出来。而且那个该死的采花贼竟然报了我名号,现在一过去,我就得完蛋吧!”
“别急。”连翘从巷口走出,手中握着一张皱巴巴的通缉令。
“连姑娘……”一缕春看到她先是眼前一亮,又看到她手里的文书,心猛地一沉,绿眸中的光芒黯淡下去,下意识想缩进更深的黑暗里。
连翘没有靠近,只是将文书轻轻放在显眼处,目光坦然地迎向他眼睛:“我看到告示了。‘淫辱官眷,杀害朝廷命官’。”她顿了顿,“我不信。”
这声不信说的斩钉截铁,没有任何犹豫。
一缕春愣住了,绿眸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光芒,眼神感动中夹杂着复杂。这已经是第三个毫不犹豫信任他的人了,他看见自己莫名成了通缉犯,都犹豫了一番。没想到这一路走来,每一个人都相信他,这大盗当的没有一点说服力啊。
他虽然是这样想,脸上表情却颇为动容,鼻子都有些酸,像是要哭了。
“但光我信没用,”连翘目光锐利起来,“得让能帮你的人信。王小姐是苦主,也是关键。她若能开口指认真凶,比你潜藏在她身边冒险套话强一百倍。”
一缕春苦笑,“她?她现在恐怕恨死一缕春这个名字了,怎么可能信我?”
连翘沉吟片刻,忽然问道:“你身上,可有……不那么扎眼,又能证明点身份的东西?”
一缕春一愣,从系统中掏出一个木质腰牌,上面刻着“巡检”字样——这是他第一次偷荷包失败,反手借来的。“这个?有什么用?我又不会易容术。”
连翘伸出手,掌心向上,眼神平静而坚定:“给我。”
一缕春迟疑了一下,看着连翘那双沉静的眼睛,最终还是把腰牌放进了她手里。冰凉的木牌落入她温热的掌心。
“你……你想做什么?”一缕春若有所觉。
“帮你。”连翘收拢手指,握住腰牌,仿佛握住了破局的关键,“也帮那位王小姐。”她抬眼,目光悲悯,“她失了清白,又痛失亲长,此刻处境,恐怕比你更绝望。”
片刻后,连翘被引入一间弥漫着浓郁药味的内室。王小姐蜷缩在靠窗的软榻上,裹着厚厚的锦被,脸色苍白如纸。
她眼神空洞地望着紧闭的窗,对连翘的到来毫无反应。身边侍立的丫鬟眼睛红肿,一脸警惕和哀戚。
连翘挥手示意丫鬟退到外间,她缓步上前,没有立刻亮明身份,而是站在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声音沉稳,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平和:
“小姐,府衙派我来,是想问问那晚……除了那个‘贼人’……你可还看到别的什么?或者……听到什么特别的动静?”她刻意用了“贼人”这个模糊的称呼,而非“一缕春”。
王小姐身体瑟缩了一下,睫毛剧烈颤抖,却依旧沉默。
连翘并不着急,她走到桌边,拿起茶壶,倒了半杯温热的花茶。她没递过去,只是自然地将茶杯轻轻放在小姐触手可及的榻边小几上。
“窗外的槐花开败了,”连翘的声音依旧很轻,带着一种家常的、近乎闲聊的平淡,“花瓣落了一地,也没人扫。我进来时,踩碎了几片,怪可惜的。”
这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终于让王小姐空洞的眼珠极其轻微地转动了一下,视线模糊地投向连翘的方向,但依旧没有焦点。
连翘捕捉到了这一丝细微的反应,继续用那种平铺直叙的语气说道:“我家巷口也有棵老槐花树。在我小时,我的母亲会去捡落花,晒干了,缝进枕头里。她说,香,能安神。”
她顿了顿,仿佛真的在回忆,“其实安不安神不知道,但她枕着那个枕头,咳喘的老毛病倒是轻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