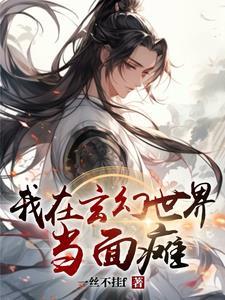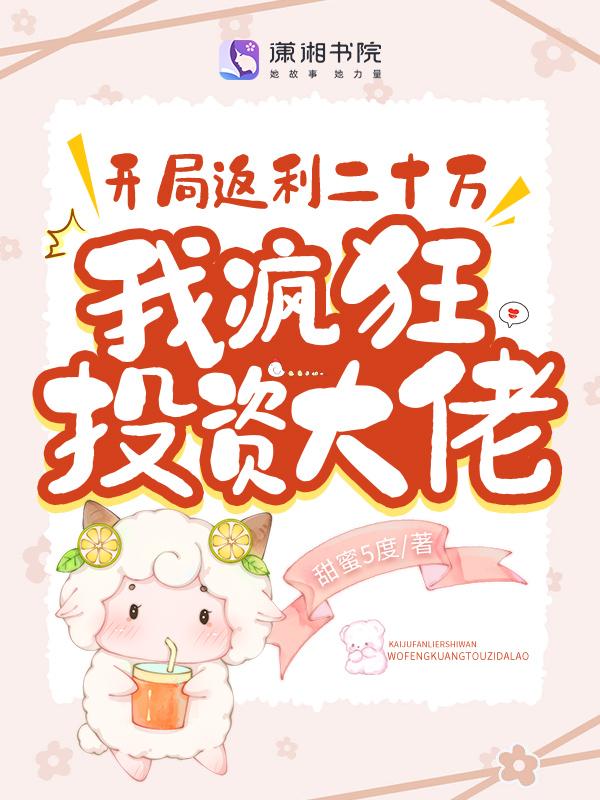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别离枝 > 第 11 章(第2页)
第 11 章(第2页)
新帝上位后,命人暗中调查前朝未尽的沙毛钱案。谢闻离京前,孙向愚曾嘱咐他道:“沙毛钱一事可大可小。就这么一枚小小的铜钱,涉及盐铁三司、提举坑冶司、转运使司以及各地监场,你说,这其中哪一处不是由皇亲贵胄把持着?以你一人之力,岂能撬动这么多座大山?”
谢闻听罢,只沉默着点了点头,但孙向愚许是太了解他这个徒弟,最终长叹了一口气道:“你的脾气,也是该磋磨一下了。”
谢闻道:“老师,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稻改以后,春、秋两贷虽纳利极少,但皆需以钱还贷,若百姓所还之钱中混入那沙毛钱……”
见师父端着茶盏不语,谢闻稍低了低头,说:“老师您也曾教导我,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陛下既然派我去查此事,便是要我一查到底罢。”
孙向愚重重放下茶盏道:“莫要打草惊蛇。”
由此,趁着雨势瓢泼,各州颓乱之际,谢闻带着亲随从静江府南下。
谢闻心里清楚,自他踏出静江府衙的大门,各州府便会接到线报。那封递入京里的密报虽意指柳州铸钱监便是私铸沙毛钱的主谋,但他却觉得似有人刻意引他前去探查。
仅从铜料上来看便疑点重重。
广右产铜极少,即便是要铸沙毛钱这样含铜量极低的钱币,也需额外的铜料。然而,无论是漕运还是矿税,谢闻查阅以后并未发觉官铜的数量核对不上。
不过那日,亲随何昉的一番话却给他辟了一条路。当时,何昉被唤进屋内点灯,发现昨日的油灯里尚有许多灯油,说:“这省油灯在广南所耗竟比在汴梁还少。”
谢闻从书案前抬起头,看了一眼那小碗状的绿釉灯,释道:“广南天气炎热,水温与油温相差甚远,且水汽蒸腾得快,反而能够省油。”
他说到此,突然眸光一闪道:“何昉,你倒提醒我了。”
何昉不知谢闻想到了什么,但见郎君眉目见喜,起身出了屋子。
数日后,谢闻快马扬鞭,在雨幕的掩映下拐道来到了桂平县,从监牢船中救下了这位名叫李榷的囚犯。
李榷为官府打上烙印的惯偷“掠子手”,其父本是世代为匠户的铁匠,因无钱缴纳代役金,在广南东路的祯州铸钱监服役数年,后因工钱被克扣出逃为流民。据说,此人在铸钱监时曾使过一种铁炼铜的法子,用同等重量的铜镏,与旧法相较,能增加铜的产量数倍。
李榷的父亲出逃后,流转于广南西路的几座私矿,攒下些许钱财成家,得李榷一子。他们家在本路无籍,李榷幼年矢怙,在街市间混迹长大,好行剪绺偷窃之事。此人屡屡被抓,积案盈寸,最终于年初因盗窃二贯钱却失手杀死事主遭捕,被判流配琼州。
方才李榷瘫坐在那,神志不清,却言之凿凿说自己只是随同乡去过那处地,谢闻知道,他被招募必然是因为他父亲的炼铜法。只不过不知他是真的意识到那处不对劲后逃走,还是因为无法效仿其父,被赶了出去,亦或是他已然交出了家传的炼铜法,才得以保全信命。
他最初提阅李榷的犯案卷宗时便发现些端倪。
文卷上书,此人于夜里在街上窃了一人二贯钱,第二日那失主在家中被发现遭利刃刺死。谢闻想,李榷这样的掠子手总不至于钱财到手又尾随至屋内杀人,此案疑点颇多,似有人想将李榷暂时移徙他处,最终出此下策。
为救李榷,谢闻命人在水下布置木石撞击船舱,虽溺死几位重犯,但其人多是作奸犯科之辈,又寻来了仿照李榷身形的尸首,瞒下了他尚存于世一事。可惜经这一折腾,李榷俨然半截入土,谢闻知道即便再急迫,也需等他恢复气力,才能从其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
这一等,便过去了一天半的时间,李榷一直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人也发起热来。
第二天傍晚,向来沉得住气的德庆有些坐不住了。他知道谢闻这一趟来桂平是利用从静江府到柳州的间隙而行,时间愈长,郎君不现身柳州,那背后布局之人恐会知晓谢闻另有打算。
“郎君,若他一直不醒,我们当如何是好?”德庆忧愁道。
谢闻沉吟半晌,道:“今夜他若还不醒,我只能留你在此地,待他醒来后一路护送他和黄笤回静江府。”
德庆知道谢闻这是准备动身了,立刻反对道:“郎君,若我走了,何人护你!”
“何昉在即可。”
“何昉功夫不如我。”德庆一字一顿道。
“所以才让你送他回去,此人是目前唯一的人证和线索。”谢闻沉声道:“有多重要自不必我多说。”
德庆知道,谢闻下定主意之事无人能改,入夜后,他只好目送谢闻带着何昉和另一位亲随冒雨上了路,往那柳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