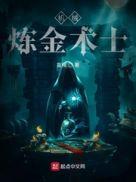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诗吟刀啸 > 2430(第12页)
2430(第12页)
凌岁寒虽见她通身富贵打扮,怀疑她是否出身权贵豪门,但实在思索不出她在这种事上说谎的理由,又想无论如何,反正她绝不会是长安豪家的女儿,不然她既已进入了长安城,怎么不回家,反而要住客栈赁房子?
心下登时一阵失落,凌岁寒低下头沉默了会儿,忽然又觉好笑,自己是在期望什么?即使舍迦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难道自己如今还能与她相认吗?
谢缘觉见她脸上露出苦笑表情,狐疑道:“你在笑什么?”
“我……没什么……”凌岁寒仰头望望冷月,“只是感觉世事难料,白天看了那么多宅子都不满意,万万没想到晚上反而住在了这种地方。”
更没想到,她会和她原本看不顺眼的人暂住在同一座宅院里。
谢缘觉侧首瞧了瞧一旁窗台的蜘蛛网,继而再次将目光移回到了凌岁寒的身上,忽问道:“你是不是有洁癖?”
“我?这种地方,是谁都会看不惯的吧?你便因此觉得我洁癖吗?”对谢缘觉的这句提问,凌岁寒很有些不解,她的确从未住过如此破烂的房屋,毕竟召媱爱享受,居室不要求那么多富丽堂皇,却必须得舒适。然而她若是真的完全忍受不了这样的环境,她也不会踏进此地。
十年前她已在心里告诫过自己,她已不是从前的凌澄,无论什么样的险恶环境,她都必须忍受,必须承受。
何况这儿只是有些破旧脏乱。
谢缘觉摇摇头,道:“从昨日到现在,我见你始终穿着白衣。”
那些所谓的白衣翩翩的侠客,大都存在于话本故事里,真正要在江湖武林里闯荡,风餐露宿,穿一身素白太不方便。谢缘觉想来想去,才会突然试探性提出方才问题,岂料凌岁寒听闻此言,一怔,神色明显严肃起来,顿了会儿,语音郑重:
“我还在孝中。”
前朝古人为报不共戴天之仇,终身素服,不听乐。自从凌岁寒在史书看到这个故事,便已在心中暗暗发誓:
——父母大仇一日未报,她一日不会除服。
而此时若是旁人听到凌岁寒这般回答,必定愧疚不安,只道是自己失言。谢缘觉依然很平静,暗暗思索:如此说来,她的父亲或者母亲离世还不到三年?那她……的确不可能是符离……
谢缘觉再度感到失望,欲言又止,终究是忍不住问道:“你孝期未过,来长安做什么?”
凌岁寒闻言静思一阵,偏着头端详她一阵,倏地道:“你像个真人了。”
谢缘觉不明所以:“我不是真人,还是假人吗?”
“昨天我初见你时,你的确很像一个假人,好像这世上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引起你心里丝毫的波动。但今天,你至少会对一些事感到好奇。”凌岁寒道,“那么,你好奇尹螣和重明吗?”
“我为什么要好奇她们?”
“那株树虽然枝繁叶茂,有人上树,通常情况下很难发现,但那男子既想打鸟,总要抬头往树上瞧,却瞧不见树上的大活人,要么他是瞎子,要么……尹螣的轻功也很不错。”
突然提起尹螣的疑点,一来是为了转移话题,凌岁寒必然不可能回答自己如今重回长安的真正目的,她便得让谢缘觉思考起别的事;二来不管怎么样,她和谢缘觉认识得早一些——早一天也是“早”——即使之前互相看不顺眼,现在关系仍没多好,但在谢缘觉和尹螣、重明这三人之间相比较,自然是后两位更让她感到陌生,她满腹疑窦,此时此刻唯有与谢缘觉讨论。
“你刚给尹螣看了伤,能看出她会武吗?”
“她受的是外伤,不是内伤,我只看了她身上的伤处,不曾为她把脉,看不出她是否修炼了内功。”
“你要为她把脉,她身为病人,也不能拒绝,你一点也不好奇吗?”
谢缘觉摇首。
好奇。所以她更要强迫自己不好奇。
凌岁寒被她的反应噎了一下,深感自己刚才说的话为时过早,原来她还是像之前那般疏离、似乎对万事都不关心。既如此,凌岁寒也不欲再与她讨论重明的奇怪之处,刚转身准备离开,忽想起一事,从怀里拿出两个药包,给谢缘觉递了一个。
“你说的避虫驱鼠的药粉,我给了重明和尹螣一些。这包,能卖给我吗?”
倘若是别的物件,她绝不会开口向谢缘觉讨要,但今夜的情况特殊,她可不想与虫鼠同住一屋。
谢缘觉道:“这不本就是你花钱买的吗?”
凌岁寒道:“但方子是你开的。”
谢缘觉道:“我开的方子,你出的钱,我们两不相欠。”
“好,两不相欠。”凌岁寒道,“告辞了。”
夜色昏昏影幢幢,不一会儿,凌岁寒的背影便消失在无边墨色里。谢缘觉的目光仍透过残破的窗户,望着院里随风摇曳的树枝,不自禁地忆起月前她离开长生谷时师君对她说的那番话。
她越发承认师君说得不错。
“你心思敏感多情,一旦出谷,那些红尘俗事只怕会让你修炼了十年的静气功夫毁于一旦,你真的考虑好了,决定好了吗?”果不其然,自己才到长安的第一日,不仅误了用膳的时辰,心中还数次生起微澜,对这么多的人与事都产生了好奇。
可是谢缘觉不后悔。
纵然师君强烈反对她到红尘走这一遭,到如今她也始终不后悔。留在长生谷里,继续孤独地看那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或许的确能多增加两三年的寿命,活到约莫二十五六岁,然后她的生命凋零在尘土里,无人知晓,又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