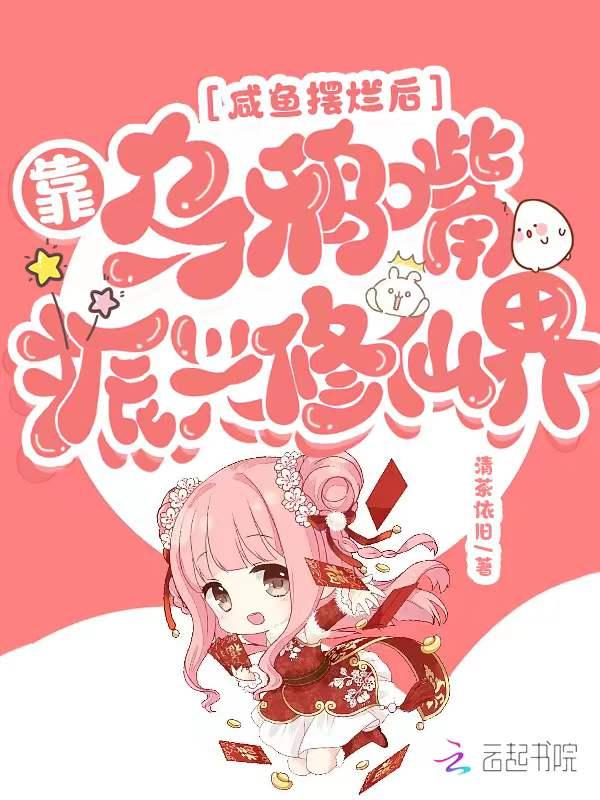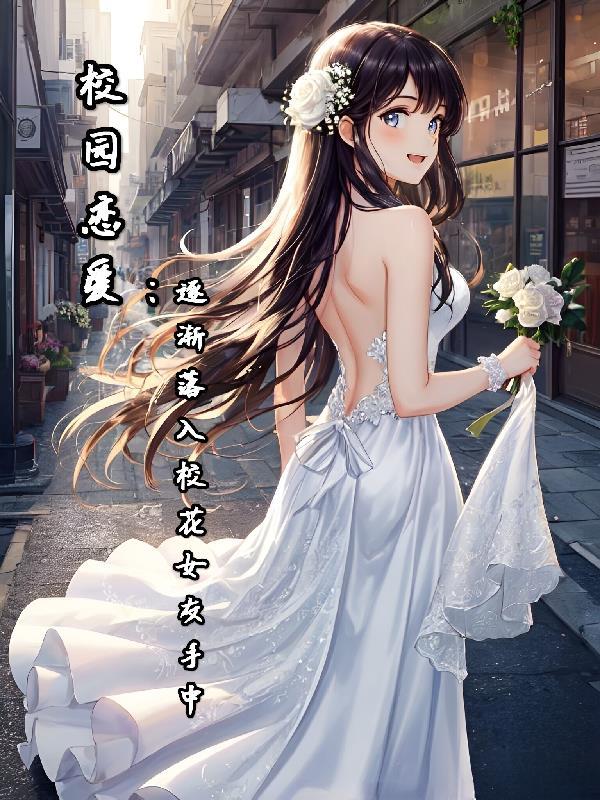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行尸走肉之弩弦与剑鞘 > 来不及哀悼(第1页)
来不及哀悼(第1页)
当行尸涌入监狱时,萨莎和鲍勃从管理楼逃出去,他们相依为命,在丛林中兜兜转转,如堕烟海。监狱毁灭的第二天,清晨的迷雾里藏着许许多多的行尸,露水浇透了衣衫,他们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不曾放弃,坚信一定能找到大家。
“我刚到监狱时心想,时间流逝,还有多久其他人会死光,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因为我害怕,才发生了糟糕的事,有些事未必会发生,我不必害怕,如果我们没有找到大家,并不意味着大家死了。”鲍勃跟我和达里尔外出觅食,萨莎一个人留在木屋做清扫,他忽然这样说道,我和达里尔愣了愣,听他继续说,“病毒那段日子,我滴酒未沾,也睡得着了。我意识到你们和我之前跟的那两队人都不一样,他们死了就是死了,我可以独自上路,但离开了你们,我只想寻找。”
我开起玩笑:“你长大了。”
“是啊,你长大了。你和萨莎找到了我们,我们还会找到其他人。那些人我了解,不会那么轻易死的。”谈笑间,达里尔的箭矢射中一只野兔,野兔的旁边站着一只行尸,鲍勃抢在我前头杀了它,捡起野兔后我们继续打猎。
太阳升到头顶,我们回木屋修整。萨莎把屋子简单收拾干净,屋子里有两间用来休息的狭小房间,一间属于先前被达里尔杀死的两只行尸,我在房间里发现了它们夫妻两人的合照,而另一间是摆放着床的书房。达里尔他们正准备午饭,我打开主卧的衣柜,里面堆满了男女主人的衣物,我拿出一套比了比,换掉身上脏兮兮且散发恶臭的衣服,走进卫生间捧起桶子里漂浮有蚊虫尸体的水洗了把脸。
我们打猎得到的三只野兔勉强够饱腹,四个人住在木屋一同度过难熬的时光。
达里尔找来一幅我想要的地图:“附近有铁路线,我们可以沿着铁轨走,如果其他人看到了铁轨,也会这样做。”
吃完了午饭,萨莎和鲍勃就分别去卧室和书房睡觉休息,他们太累了。我抱着朱迪斯的兔娃娃,与达里尔守在客厅,他坐在凳子上用匕首削木做箭。
“达里尔,你会怀念以前吗?”我望了一眼静悄悄的窗外,迟迟不听他回应,于是转过头去看他,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像是想起高兴的事情莫名其妙地笑了。
“会,在监狱我们都过得很好,有过困难,我们都挺了过来。”
“我不是说监狱,我是指末世以前,你原本的生活,比如……莫尔。”
他的笑容凝固,垂下眼眸:“我不知道怎么算怀念,有时候会想起。”
“人一旦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兔娃娃被我放在窗台,我走到达里尔身后,弓身圈住他的脖子,紧贴他的后背,“我不相信有人生来就坚强得宛如铜墙铁壁,我一直很想说,你要是有什么难过悲伤,都可以告诉我,我虽然不太擅长安慰人,但我擅长聆听,你知道的,我希望你们,希望你一切都好。”
达里尔蹭了蹭我的耳朵,牵过我的手亲吻:“我知道,你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安慰。过来,我也有点困了。”他放下匕首和木箭,领着我坐到地毯上,我们面对面坐着,他让我的双腿环绕他的腰,他的脑袋倚靠我的肩膀,我们依偎在一起,他一说话,我就觉得肩头颤动,心也颤动。
“我父亲虐待我们,我不想他,可他是我的父亲,我不得不想。他死那天,我很高兴,也很难过,高兴他再也打不了我了,难过我没有了父亲。还有莫尔,他同样打过我很多次,他是我哥哥,所以我任他打任他骂,只要他不离开我怎么都行。”人生就是在不断的相遇与告别中度过的,哪有谁会不离开谁呢,达里尔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但是我们害怕离别,不愿意离别,“莫尔还是死了,我接受了他的死,就像我接受父亲的死,只是花的时间更长。我不惧怕死,惧怕的是死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从亚特兰大到现在,我们见过太多离别与死亡,早已麻木。没有谁会永远陪着谁,没有谁会时刻与谁不分开,所以我格外珍惜和你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正如你说过的,我们是家人。因为你们,我混蛋的生命有了意义,因为你,我刚说的‘接受’有了例外。”
他总是能自己安慰自己,自己说服自己,他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别人发现他开始伤心时,他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
“你和我,不止是家人,”达里尔的头发湿漉漉的,他流了满头的汗水,我用额头抵着他的额头,他漂亮的蓝眼睛闪烁着水光,睫毛轻颤,我轻轻抹去他眼角的泪花,“就像这样,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需要憋着,不需要隐瞒。”
他吸了一下鼻子,搂我更紧:“谢谢你,安。”
“不必对我说谢谢,我既然说我们不止是家人了,跟我客气做什么。再说了,我还欠着你好多次道谢没说呢。等我们找到瑞克他们就好了,我们会团聚,然后一起寻找下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在新的地方安居,过上和监狱时一样的生活,甚至更好。”亚历山大就是那个地方,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那里。
“嗯,我们会的。”
我抚摸他的背,用哄朱迪斯睡觉的方式安抚达里尔:“你们从外面带回到图书室的书里有一句话,‘世界上的水都会重逢,每条路也都会带我们归家’。我始终认为家不是固定的地方,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我们都会回家的。”
这个晚上,我和达里尔携手而眠,木屋的地毯说不上厚也说不上薄,总之躺在上面还算舒服,不过是因为有达里尔在身边,所以无论是哪里,都称不上糟糕。因此我们一觉睡到天大亮,达里尔比我还晚醒,阳光从门窗的缝隙投射进来,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估计脑袋还没彻底清醒就下意识地背起弓弩准备上路了。
我们在木屋都换了一身干净的行头,我拿了木屋主人的背包,把兔娃娃装了进去。根据地图的指示,我们得穿过身处的树林,先走到公路上,然后再行个半小时左右的路程,就可以看到铁轨。
公路通向监狱,如果监狱的大巴逃出去一定会经过的,我想到这,脑中全是乘坐大巴的众人被行尸杀死的场面,他们惊慌失措,大喊大叫,白费工夫,拼命拍打门窗却激起了行尸的欲望,行尸犹如滴进水中的黑墨迅速扩散,一只行尸变成了两只行尸,两只行尸变成了四只行尸,几分钟后,整个车厢塞满了面目狰狞,伤口遍身的行尸。
我晃晃脑袋,强迫自己不去想这恐怖的一幕,可是我眼前的幻觉仍未消失,那辆载着行尸的大巴就停在公路的正中央。
“萨莎!”她不顾一切地奔了过去,大巴内寂静无声,我试探地敲响车外的铁皮,没有行尸活动的迹象,“有其他人来过。”
我们绕到车门处,车门被打开,地上累着数十具行尸尸体。达里尔查看行尸头部的伤口,判断在一两个小时前,接着我们一一核验行尸的身份。
迦勒医生、理查德小姐、丽兹与米卡的父亲、大卫、凯伦……
我们来不及为他们哀悼,生存不易,死亡才是常态。
“他们应该刚离开不久,说不定就是带着朱迪斯的人,我们能追上去。”
达里尔赞同我,他点点头,迈开了步子。
我呼喊发呆的萨莎:“泰尔西肯定还活着!他很厉害,也许就是他带着朱迪斯呢,我们得去找,我们不能停!”
萨莎回过身,她猛吸一口气:“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停!”
今年的夏天没有往年炎热,风中带着悲苦的凄凉,我们四个人一刻不停歇地走着,不曾注意头顶太阳的轨迹,不曾关注两侧丛林内游荡的行尸,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只有一个,那就是铁轨。
差不多半个小时后,我们找到了。
铁轨坐落于树林中,我们为向哪个方向走产生了争执,鲍勃与萨莎意见不统一,我和达里尔研究着地图,四个人得不出结论。我叹着气,心想那该死的食人魔们把终点站的牌子树在了哪里,毕竟如果我们不能在路上与众人团聚,就只能去终点站闯一番。
我朝着铁轨的两个方向张望,有一边走来一只行尸,反正大家还没商量出结果,我决定活动活动筋骨,索性提着剑上前杀死了行尸。刚好我走到铁轨的拐弯处,远方树立有一块木牌,我赶紧招呼众人跑过去。
这木牌果然是食人魔的,牌子下面挂着一张地图,每一条用红线标注出来的路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名为“终点站”,而木牌上赫然写着几行大字。
“避难所欢迎所有人,抵达就能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