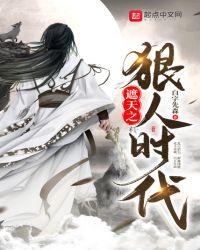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桃夭定终身-高冷帝君漫漫追妻录 > 卫乱(第1页)
卫乱(第1页)
新年过去,季节更替。农人又开始了春收、夏播、秋收,似乎一切如常。只是有些人的生活却不寻常的忙碌起来,比如公子朔。
自开春来,他已和自己在卫国的势力密会了几次,有时卫国的几位臣子亲自到齐国来见他,有时他派了人到卫国去密谋一些事情。
他离开卫国已经六七年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尚是个半大孩子。十一岁的孩子继位,他不相信身边任何一个人,只会用王权去威慑、去镇压,结果才做了三年国君,便被国内的大臣合谋推下了王位,幸得他的母亲是齐国公主,他才保全了性命,逃难到齐国。
离开的时候他才十四,如今他已经二十了。多年的寄人篱下,让他的变得隐忍、随和并且体察人心,若是和人初识,别人几乎会认为他是一个和善而没有野心的避难公子,而绝不会联想到他曾是年纪轻轻便设计杀害了自己兄长和当时太子的残暴少年。
这些年,诸儿年年赏朔财宝,让他运回卫国偷偷打赏笼络那些曾经拥护他的臣子,让他们帮忙留意卫国朝堂的动向,并一步步扩建朔的势力和圈子。所以朔不在卫国这些年,不少大臣非但没有忘记这个曾经的国君,反而越来越多人称赞起起这个国君的好处。
卫国现今当政的是公子黔牟,当时左右公子恨公子朔残暴,趁朔出使他国,借着民愤拥立黔牟做了卫君。
可当黔牟做了国君后,左右公子却有了新的烦恼。
黔牟的母亲夷姜自小国嫁入卫国,借不了母族一点力量,又名声欠佳,早年逝去,因而黔牟在登基前在国内几乎毫无根基。
左公子本以为黔牟没有背景,登基后方便他和右公子大展拳脚,可惜卫国虽是天子封的大国,经济尚可,无奈军事上十分疲软,国内更无能征善战之士。
以前和齐国结盟时,其他诸侯还愿意假以颜色,如今换了国君,连一些小邦都跃跃欲试,在卫国边境三番五次挑衅。
前年遭了旱灾,官府却拿不出赈灾的财物,民间抱怨叫骂声不绝,朝廷中不知是谁起了头开始怀念以前公子朔在位的日子。
情绪一旦形成暗涌,就好似渗透到宫里的每一个角落。黔牟心中恐惧,但除了置若罔闻,别无他法。
如此几年下来,诸儿感慨自己的苦心总不算白费。因而待攻下纪国,心中第一要紧之事便是送公子朔回国。
这年腊月,诸儿约了鲁国、宋国、陈国和蔡国共同助公子朔回国,郑国本来亦在诸儿的邀约名单中,但郑国曾和陈国、蔡国不和,子仪为了不让诸儿为难,便以身体抱恙推脱,没有前去赴会。
诸儿去年已和鲁君同形成默契,愿意和齐国共进退。宋国、陈国和齐国有姻亲之好,正在寻找机会和齐国重温旧谊,如今齐国既有召唤,大家自然愿意赴会。
寒风中的朝歌人潮涌动,无数车马和士兵在城外扎起了帐篷,有一种异样的热闹。这次攻卫,诸儿并没有安排太多的兵力。
攻打卫国的主要目的在于逼现今的卫君黔牟退位,送公子朔回国重新继位,他既不愿意真正兵戈相见,让朔接手一个残破的卫国;亦不愿意杀了黔牟,杀戮鲁国先君允和郑国先君子覃的恶名在前,他绝不愿意再做同样的事情。
因而这次攻卫声势是浩大的,但是几国加起来不过两万余兵力,齐国出一万兵力,其余一万,则由其余几国各派了几千兵士来壮大声势。
朔眼见兵力无法和攻纪时相提并论,心中不由担忧战事的走向。但他知道除了齐国,其余几国愿意帮他夺位不过是看在齐国的面子上,而绝非他对几国的空头许诺。
诸儿曾提醒他郑国的前车之鉴。当年郑国子突为了上位曾许诺了他的盟国宋国无数好处,待宋国助他上位后,他不堪宋国的盘剥和宋国反目成仇,以至于最终又丢了王位。
所以朔这次只是许诺齐、鲁,陈,蔡少量的金银珠宝作为代为出兵的酬劳。
冬季围城,诸儿有自己的打算。腊月本是合家欢聚,准备迎新的时节。若在此时围了朝歌,城内百姓的怨怼和恐惧必比一年其他时刻更甚。
过了年,大家要到城外准备春耕,若城里的百姓出不去耽误了春耕,那更会耽误了一年的好收成。围城的要职在于做足声势、扰乱人心,以至于不攻自破。
朝歌城内此时却是一片恐慌寂静,和朝歌城外的炊烟缭绕似乎是两个世界。
最煎熬的自然是黔牟本人,自四国围城以来,他已经派人向几个国家发了密函,可是除了周天子外,竟无一个国家回应,真是应了屋漏逢旧雨,鼓破众人捶。空荡荡的朝堂内,黔牟望着一向能言善辩的左公子职和右公子泄。望着二人表情呆滞,黔牟忍了多年的怒火终于喷射而出。
"两位爱卿,为什么哑了?你们不是一向胸有成竹吗?你们说说如今这围困之势怎么破?当年是两位要力荐我做国君的,如今我要失了势,新国君还容得下二位吗?"
左公子颤颤巍巍,不敢看黔牟的眼睛,说道:"或许等天子派的救兵来了,咱们就有救了呢!"
"哼!天子?天子的威严如今除了各国在拉大旗、装点门面时有用,其他时候何曾有半点用处!"黔牟讥笑。
右公子望着远处几近发狂的黔牟,心中无数幻境飘过,若是回到八年前,他还会和左公子策划那场政变吗?
当年他也曾犹豫过,有人劝过他:"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強。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
黔牟既无先君之宠,又无母族之势,更无强臣之援,此为无本;登基后黔牟无度量、无智谋、无治术,在民间也无佳名,此为不枝。
一棵树,根基不牢,又缺乏阳光雨露,如何能长成参天大树呢?恐怕这场围困,他难逃此劫。可是怪谁呢?谁能想到当时民愤汹涌的朔,几年后还回杀个回马枪呢?
过了腊月,又下了两场雪,然后天一下子就暖了起来。天朝派的援兵终于到了,只可惜还没有进城,就在朝歌外的混战中铩羽而归。
城里的气氛原是寂静中带着恐惧,另带着一点点被救援的期盼。当这一点期盼的幻想被戳破,恐惧就无法遮掩了。
城外有消息传来,说此次四国围城只是替卫国行天道,送流浪在外的卫君回国,而非要百姓受苦。
这一点点消息如星火燎原,点燃了大多人的怒火,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卫宫城门前示威叫嚣的队伍了,只有极少人会记得数年前,也正是他们的要替天行道的正义感才逼了朔退位。
宫墙外的喧闹声持续了半个月,待到二月底,王宫里的食物也渐渐不够了,黔牟内外交迫,他知道再无可能扭转时局,便托了使者到城外求和。至于对方提的条件,只要留自己的性命,其余一切他都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诸儿向天朝写了封书信,里面痛陈黔牟在即位几年的种种不作为,又恳请天王能够降恩替卫国管教黔牟。
上次攻纪胜利后,齐国主动送给周天子几个城邑。这次围卫,天王看齐国仍愿在面子上留有余地,于是也顺阶而下,按照诸儿的意思在周朝给黔牟封了个小官。黔牟死而复生,竟心甘情愿地去洛邑赴任了,此后在洛邑度过余生乃至老死,倒是有了一个安稳的老年。
清理左右公子,是诸儿留给朔回卫的第一件事。朔心中恨极了这两个人,当年他即位时年龄尚幼,两人视他为小儿,在朝堂常常越俎代庖,朔心中惧怕二人是父亲朝的老人,敢怒不敢言。
![令使很好,所以归巡猎了[星铁]](/img/14858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