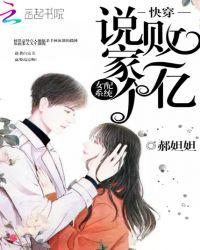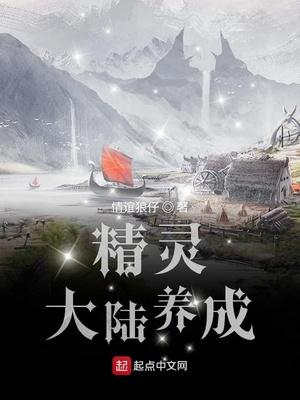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桃夭定终身-高冷帝君漫漫追妻录 > 母子(第1页)
母子(第1页)
戴氏走了,冬日的黄昏有种凄楚的荒凉。
诸儿并不怪羽裳,那个女子根本就不该嫁入宫里,如今她红杏出墙,诸儿心中竟有一丝佩服她,好歹她为自己的命运抗争过。
他心里难受的是公孙无知,公孙无知明知羽裳是自己的妃子还去勾搭,究竟两人真的是一见钟情,还是公孙并未真正把自己放在眼里?抑或是因为自己袒护了他太多次,公孙不相信自己会真正下手?
诸儿不曾发现他手中的笔杆已经被折弯了,离折断似乎只是须臾之间。该动手了,只是还需要找个合适的机会,最起码不能是这次,一国之君因为奸情而杀了他师父的儿子,他父王的爱臣,这样未免太折损自己的名声。
第二日傍晚,诸儿回了齐宫,且当夜安歇在了安乐宫。过了几日,又有不少东西赏赐到安乐宫,嘉奖羽裳贤淑识体。宫里众人摸不着头脑,流言失去了威力,慢慢就散了,只有羽裳知道那夜发生了什么。
她看到诸儿来安乐宫时,本以为是自己的死期到了。可是诸儿却问她是不是在宫里过得太苦?若她愿意,诸儿可以放她出宫。
诸儿还劝她要看清公孙无知,免得所托非人。诸儿走了后,她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原来诸儿勘破她的私情后没有半点难受,原来她在诸儿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原来公孙无知虽然出身尊贵,可若和诸儿相比,一个如朗朗乾坤,一个却如阴云遮蔽下的昏月。
这些年她对诸儿的一片痴情不过是笑话,当她明白了这一切,她对诸儿的爱意和内疚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恨。她要报复,总有一天她要让诸儿明白,她并不是从未存在过,她要让诸儿为今日的冷漠付出代价。这代价,甚至是性命。
从夏天和婉分别,如今已有半年光景。十一月初,诸儿又书信到鲁国,他不敢硬催归期,只是询问婉在鲁国的近况,同时夹杂了一些自己对婉的思念并透露自己病了一场。
其实这时他的病已大好了,只是想通过卖惨来获取一点婉的柔情。果然婉的信很快便到了,信上说她月底便会返齐,届时子同会送她回临淄。诸儿虽然得知子同一起访齐有些疑惑,但想到很快便可以见到婉,心中还是不由地盼时间走得快一点,乃至在宫里早早开始让下人准备婉平时爱吃的食物了。
婉回到鲁国后并未回曲阜,而是照旧在欢城住了下来。她在欢城的喜舍居平日有人看护打扫,再次归来似乎只是出了个远门,一切依然是那么适宜。婉希望在这里和子同相见,可是她等来的不是同,而是友。
婉已经几年没有见过友了。对于这个孩子,当年她心中有更多的放不下,也更无颜去面对。
友自出生后曾出宫和她过了几年相依为命的日子,后来回宫后依然由她自己养在凤藻宫。友自幼聪敏,小小年纪却好似和她心灵相通。当年她对友有多少爱意,后来的种种就让她有多少愧疚面对这个幼子。
允去世后,婉从不敢去向子同要求去见友。没想到几年后,友却主动来寻她了。眼前的少年几乎赶上她的身高,清秀温和的眉眼中有着一股疏离的气质。婉强压下眼中的泪花,上前拉住友的手,说道:"友,你好!"
来到室内坐定,婉忙叫阿娇端上好的茶水,四目相接,两人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是好。最后还是婉开了口:"友,你长高了,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兄长待我很好,挑了上等的宫女伺候,还给我找了专门的教习师傅。"婉看着友瘦弱的肩膀,一个孩子,从九岁到十三岁,父亲去世,母亲不在身边,就算锦衣玉食,婉亦可以猜测友的人生会经历什么样的动荡。
"如果阿娇回去伺候你,你觉得妥当吗?"婉问道。友幼年时和阿娇关系最好,婉想,自己身份不便,也许阿娇可以替她陪伴这个孤独少年的成长。
友轻轻摇头:"我大了,母亲不必再替我忧心。母亲,你这几年过得还好吗?齐王对你可好?"
婉眼泪再也忍不住掉落下来,友看着灯光下母亲那颤抖的极力忍住眼泪的脸,眼眶也渐渐湿了。"母亲这辈子做错太多事,不敢祈求你的原谅,只求以后若有机会,可以稍作补偿。"
"母亲,只要你现在快乐,那便不算错。"婉抬头望着对面的孩子,发现友的眼睛如此澄澈,像极了幼时看她时的样子。
"孩儿记得有年冬天,有一位公子曾带我们去城外游玩,母亲说他是一位重要朋友。他,可是齐王?"友问道。
遥远的记忆袭来,婉惊讶友还记得那么多年前的事。她略带尴尬地点点头。"友,你真是好记性。"
"母亲,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比那一天更快乐的你了!如果那个人就是齐王,你便不用对孩儿有什么遗憾。"
婉把友拉过来,希望像孩童时把他抱在怀里,可友只是轻轻地靠在婉的肩头。屋内寂静一片,但有暖流在涌动,抚慰着这对母子的离愁别绪。
友在欢城住了十多日,这期间,她断断续续听友讲了鲁宫的一些事情。
友能有如今的状态,和子同对友的态度密不可分。当年庆牙叛变未果,但是给子同上了生动的一节课,诺大的鲁宫,父母俱不在,身边人心莫测,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友,那是他身边唯一的亲人,当他把友叫到自己身边时,他发觉这个弟弟和他一样在默默用力度过那段晦涩的时光。
友年龄小却早慧,有一双极像母亲的双眼。他故作坚强的样子让子同心中生了做兄长的气概。若他护不了弟弟周全?又谈何治理好一个国家?于是,婉不在的这几年,倒是催生了二人的兄友弟恭。
友临走的时候邀请婉回曲阜,婉拒绝了。那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她如今再无勇气踏足。她只是请求友带消息给同,让同有空的时候可以到欢城见上一面。
待友回到曲阜,便听到了诸侯间传得沸沸扬扬的那场夏末的惨烈的大战。齐国率近十万大军在短短两日内便攻陷了纪国国都,纪国公离国别家,齐国接管了纪国。
这一切如同飓风,在各个诸侯国间掀起了巨浪。这个相邻之国,国君曾险些丧于自己手中,如今却让所有诸侯颤栗。
同多个夜里辗转反侧,反复衡量和齐国的相处之道。若要日后的安稳,和齐国建立邦交怕是唯一的选择。他做了几年国君,渐渐明白意气用事的代价,有太多的事没有对错只有利弊,有太多的时候也由不得他,尽管他是名义上的国君。
鲁国若真想和齐国建交,相较他国有天然的优势。他为何不好好利用母亲这个桥梁呢?至于前仇旧恨,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早已不是他目前心中最在意的事了。
因而子同给在欢城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登基后齐鲁两国国君尚未正式会晤,他仰慕齐王威武,希望有机会和齐王相见,再续齐鲁旧谊。
婉看到这封信时百感交集,子同终究是成熟了,开始有了帝王的考量。两个曾经在她怀里求温暖的孩子,在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候后,走向了各自的成熟,虽然他们明明还都只是少年。
她觉得欣慰,又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也许是因为她的失职两个孩子才被迫成长,但人生就是因缘际会,且一往无前。
![一胎三宝,但男主生[GB]](/img/18940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