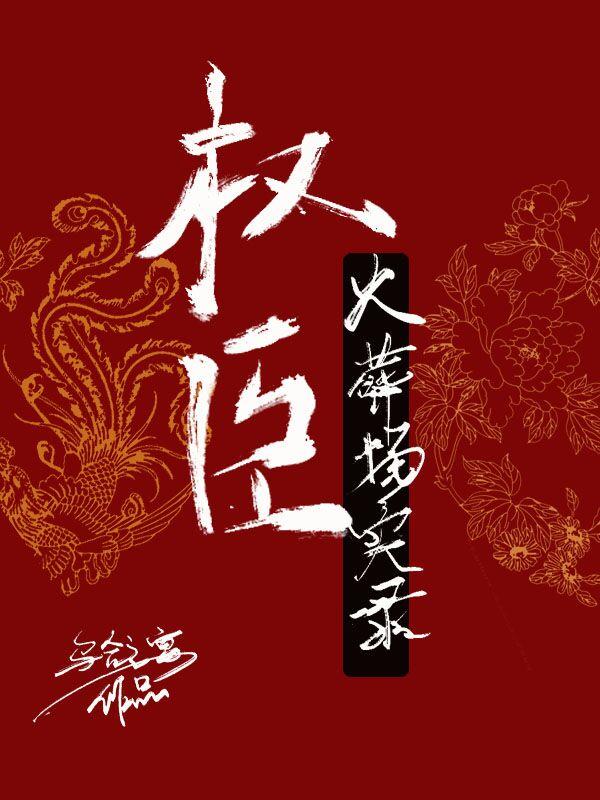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近臣 > 锋芒毕露(第2页)
锋芒毕露(第2页)
焕游笙朝服下摆沾染着尘土,乌发微乱,略显狼狈的模样立刻引来无数窥探的目光。
“焕爱卿?”皇帝的声音里藏着微妙的波动,似乎对她的风尘仆仆也颇感兴趣。
庆王被打断,脸色骤沉,抢先一步发难,声音尖利:“焕大人!今日大朝,百官肃立,独你姗姗来迟,藐视朝仪,不尊陛下!该当何罪?”
焕游笙在殿中站定,无视庆王的咄咄逼人,朝御座深深一揖。
她声音清朗沉稳,带着赶路后的微哑:“臣焕游笙,参见陛下。臣来迟,并非有意怠慢,实因卫尚书一案突有重大关隘亟待查证,臣恐误了陛下明断,故亲往查证。臣一心为陛下分忧,若有失仪之处,甘愿领罚。但恳请陛下,容臣先奏明所查之事,再议臣之罪责不迟。臣绝无怨言。”
她将“卫尚书一案”几个字咬得极重,目光坦荡。
“卫尚书一案?”庆王心头警铃大作,焕游笙此刻现身,并直言为此案耽搁,让他顿生不祥预感。
他几乎是失态地厉声质问:“焕游笙!你休要在此故弄玄虚!卫玄寅盗用宫笺铁证如山!你所谓的‘重大关隘’,莫非是想包庇罪犯,混淆视听,欺君罔上?陛下,此人心怀叵测,其心可诛!”
“元忠……”
仍旧是不轻不重的一声,不带多少责备的意味,却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瞬间浇灭了庆王的气焰。
庆王如遭重击,脸色更加铁青,不甘地退后一步,怨毒的目光死死钉在焕游笙背上,如有实质。
皇帝的目光掠过庆王,投向焕游笙。
焕游笙这才抬眼。
御座之上,皇帝龙袍依旧华贵,金冠仍然璀璨,但那张曾经锐气逼人的脸庞,已掩不住岁月和操劳留下的刻痕,眉宇间浸满深深的倦怠,连眼神都似蒙上了一层浑浊。
她心中微动,但此刻无暇细想。
“谢陛下。”焕游笙躬身行礼,声音平稳开始讲述,“陛下容禀。臣当年奉旨前往剑门关拔毒,途经鄂州。彼时曾见当地使用一种信笺,其质地纹样,与宫中御用的金花笺极为相似,若不细看几可乱真。臣当时虽觉诧异,但重伤在身,未及深究。”
“近日,听闻卫尚书因‘盗用宫笺’获罪下狱,臣心中疑窦顿生。忆及鄂州所见,遂托付一位正巧前往鄂州游历的友人,请其代为留意查证。果然,经其多方探访证实,此笺纸实为前朝卫涛娘子所仿,鄂州官衙及富户间广为使用,并非稀罕之物。”
说着,她自怀中郑重取出一份崭新的信笺,双手捧起:“陛下,此笺便是鄂州所产,仿制金花笺之物。恳请陛下御览,并与宫中真品、刑部自卫府搜出之‘赃物’三相对比。”
侍立太监立即趋前,恭敬接过信笺呈于御前。
皇帝的目光缓缓扫过三份笺纸。
无需多言,差异立显:
其一,鄂州仿笺与卫府“赃物”皆以竹浆掺青檀制成,质地略显粗糙,纹理松散,与宫中纯用上等桑皮精制、细腻光滑隐含暗纹的金花笺有所不同。
其二,宫中金花笺边缘所印的鸾凤纹饰,自皇帝登基后,为表天命所归,特意加上了象征皇权的日月徽记;而鄂州仿笺和卫府证物,其纹饰虽模仿鸾凤,却都独缺了这至关重要的徽记。
可见,从卫府搜出的所谓“证物”,不过是从什么渠道得来的鄂州民间信笺罢了,既非盗用,亦非自仿。
大殿内落针可闻,所有目光聚焦御案。
庆王额角冷汗终于涔涔滑落。
他强作镇定,在皇帝开口前急声狡辩:“即便如此,那又如何?你自己也说了,此笺纸乃前朝卫涛娘子所仿!卫玄寅与其同姓,怕是本家,此等攀附前朝余孽、私用僭越之物之奸佞,其心叵测,同样罪责难逃!”
焕游笙反应迅疾,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凛然正气:“庆王殿下此言差矣。且不说殿下拿不出这卫涛娘子与卫家有何关联的证据,便是子虚乌有。即便真如殿下猜测,那卫涛娘子生前在鄂州光明正大开铺营生,从未隐匿身份,仿制笺纸流传民间数十年之久,官府亦在使用,显然是过了明路。”
她目光如炬,步步紧逼:“既如此,为何卫尚书使用,到了殿下口中,就成了‘攀附余孽’、‘心怀叵测’?若按殿下这般‘宁可错杀一千’之论,莫非要将朝中所有与前朝略有牵连者,尽数赶尽杀绝?”
她这是极具引导性的激将之言,可惜庆王本质上是个草包,闻言果然恼羞成怒,竟口不择言,脖子一梗,脱口而出:“为绝后患,亦无不可!”
此言一出,满堂哗然。
“放肆!”皇帝猛地一拍御案,声音陡然转冷,“庆王,朝堂之上,岂容你胡言乱语,口出此等悖逆狂言?”
这一声呵斥与之前不同,可以说得上是严厉,带着凛冽的帝王之威,朝堂再次陷入死寂。
庆王脸色惨白,噤若寒蝉。
小剧场:
焕游笙:不知道的还以为庆王和我是同伙,我给一个指令,他就回一个动作。
慕容遥:敌人若是够蠢,往往比同伴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