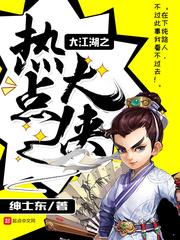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少将军他追我逃 > 牝鸡司晨(第1页)
牝鸡司晨(第1页)
横峰侧岭,被山带河,靖王一行出了京城后,与护卫军及仪仗队汇合。跨洲连郡,一路上靖王下令全速前进,如非不得已不进驿站休整,时常宿在山林间,好在冬季将近,野外没有夏日那么难熬。
山路蜿蜒,从天上往下看,靖王的仪仗队连绵数里,红色兵服,与仪仗队金色耀眼华服,裹挟在葱葱郁郁望不到边界的山林中,如一条红金交错的蛟龙,潜行千里。
日头在山带斜后方,懒洋洋滑落,带来漫天霞光,给满眼的绿晕染上些许霞粉。
卫昱祯连赶了五六日的路,纵然是安排了最宽敞的马车,装饰了最软的垫子,他也有些受不住。往日仪态端方的他,此刻也不禁坍塌了背膀。
难得地,内侍传令,停车休整,开始安排驻扎事项,走得脚起泡的众人皆心里为之一松。
在剑宁的陪同下,卫昱祯信步穿过几株老树,站到崖边,远眺前方。天地何阔,苍茫万顷相接连,山崖连绵不断,大河奔腾不息,城郭林立,日暮西山,炊烟袅袅。
远离了政治中心,挨不着边疆,人们没有纷争相扰,连地气都透出一股祥和。
卫昱祯深吸一口气,青翠的味道瞬间盈满胸腔,让人心旷神怡,他背着手,凝视着前方幽幽叹道:“真叫人流连这等中正祥和的时刻。”
“父王和皇兄不走出那天底下最高的城墙,又怎能真的听到他的子民的祈祷,所知所解,不过是口口相传的消息,每个人都暗自增添自己的私心,混杂到最后教人分不清,辨不明。”
“古人诗词卓绝,将山川河流悉数记录在册,每每阅之,皆让人如身临其境——但总归逃离不了一个‘如’字,若没有亲眼见到,所想总是不够壮丽。”
“他们,真的在围墙里呆太久了……”
前后左右,只有那弯腰驼背的老树,还有个不会接话的剑宁,难得的直抒胸臆时刻。
不知怎地,卫昱祯突然想起卫景珩——他的堂兄弟。
祖辈的隔绝,让他一日也不用在金陵接受教导,不用行为举止皆有宫人亲自教导,记录在册,无数双眼睛盯着挑错处。第一次见到他,便是在辽阔的草原,他扮作商旅,被这位素未谋面的堂兄弟黑马银枪救下。
那一面,他心里就认出了他,他的堂兄弟确实随了母亲,生得十分貌美,但眉眼间的神韵与他父亲如出一辙。他曾在藏经阁见过宁王的画像,是何等的风姿绰约,意气风发。
没由来地,看他没正经的模样,竟有些羡慕。
基于万事要全面的准则,他从没对卫景珩松懈过。
但他心里其实不觉得卫景珩可以跟他争这个天下,他卫昱祯从来都不是自己那谨慎到疑神疑鬼的父皇。
卫景珩太自由了,他虽然聪明伶俐,颇有城府,但常年浸润在军中的生活,让他有了侠义之气,这恰恰是大忌,做帝王可以有很多面的性格,但偏偏不能意气用事。
他敢断定,即使江山拱手相让,他要不郁郁而终,要不会落荒而逃。
而镇北军真正的灵魂宁王,他的皇叔,自从自己在十岁那年瞧见了他的画像,心中便有了一个小小的猜测——宁王当年或许不是争不过父王,他只是不想争。
直到见到了卫景珩,他更确信这个想法,卫景珩没有母亲,是宁王亲自带在身边教养,只能是那样光风霁月的人才可以养出来的孩子。
当年他确实是铤而走险,去北疆寻找机会,但见到卫景珩,他就知道他可以正式和自己的皇兄相争。
皇兄自诩把控内阁元老,手握城内禁军军权,在金陵他处境不容乐观,所以他要从外围开始蚕食。
卫昱祯站了一会,夕阳落得很快,四周围开始被黑暗侵蚀,他知道黑夜意味着危险,他贪恋地再瞧一眼那不再刺目的暖阳,缓慢回身。
剑宁还是太安静了啊,如果他像守墨的话,自己是不是不会太孤寂了呢。
卫昱祯被自己这个想法逗笑了,摇摇头将这个想法驱逐出去。卫景珩来信说,李家那小孙子还活着,要跟自己合作。
李丰禄的独孙,当年被人下药废了,人也废了,在京里名声不太好,从不与官家人来往,终日流连市井,活成个浪荡子弟。
然而这样的人,竟然能在皇兄那群杀人如麻的暗卫手底下活下来,还搭上卫景珩替她传信。看来也是个韬光养晦的狼崽,是留着李家军血脉的人呢。
突然,卫昱祯心里松快些,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
……
李昭微睡醒的时候,外面镖局弟子晨练的声音已经喊破天际。
她伸出自己的手,好像伸手不见五指?
这才几更天啊!李昭微胡乱撒开床帘,探出头瞧向窗户,很好外面也是漆黑一片。
她向来起床气有点大,因为身体不好,寒意太甚,心血不归,神不安,所以醒来不容易入睡。虽然现在寒毒解了,但亏空多年的身体没那么快养回来。而且在这阳气十足的呼喊声中,有谁还能睡得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