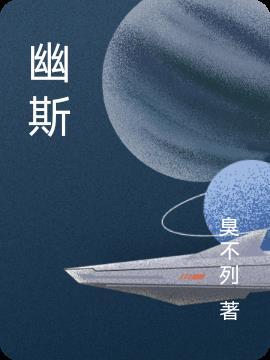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完蛋,我被公主包围啦 > 第676章 十三进士(第3页)
第676章 十三进士(第3页)
他顿了顿,见杨炯神色不动,便抛出腹稿:“学生以为,当力行‘方田均税法’与‘折漕为银’之策!”
他见吸引了众人注意,越意气风:“其一,‘方田均税法’!
天下田亩,隐匿者众,豪强兼并,赋税不均。
当遣精干官吏,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土质肥瘠分为五等,核定实际田亩数目,登记造册。
如此,则隐田尽出,田赋可增,且豪强难以再行诡寄、飞洒之弊,小民负担亦得稍减。
其二,‘折漕为银’!
江南漕粮,不必全数实物北运,可择其部分,按丰年时价折为银钱,由官府就地采买或令粮商运至指定地点缴纳。
此举,一则大大减少运输损耗与沿途盘剥之弊;二则节省巨量运力民夫,可转用于屯田或他务;三则银钱流通,利于市易,可充盈国库。
此二策若行,不出三载,府库必充,国用可足。
学生愿为朝廷,梳理这钱粮血脉。”
杨炯静静听完,暗道这引述之策,虽改头换面,却依稀可见前代能臣理财之影,更透着一股急切的功利。
他手指在粗糙的桌面上轻轻敲击着,出笃笃微响。
看向杨叔的目光愈审视,此人言辞便给,思路清晰,确能抓住财政漕运的要害,提出的方略听起来也颇有章法。
然而,杨炯眼中却无多少赞赏之意,反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
半晌,杨炯才缓缓道:“理财之道,关乎国本民命,牵一而动全身。你这两策,立意不可谓不高,手腕不可谓不精。然丈量天下田亩,触动的何止是豪强?
地方官吏、乡绅胥吏,乃至无数依附其上的小民,其利益盘根错节,阻力之大,恐非你所能想象。
前朝亦曾有人行‘经界法’,初衷甚好,然执行之中,丈量标准不一,胥吏上下其手,反成扰民虐民之政,最终不了了之,徒增民怨。此其一难。”
杨炯端起碗又放下,目光如炬:“其二,‘折漕为银’,看似便捷省费。然江南粮价,丰歉波动,岂是‘丰年时价’四字可定?
官府定价过低,则伤农;定价过高,则国库受损。
更紧要者,一旦漕粮折银成例,地方官吏手握采买之权,此中寻租舞弊之空间,比之实物转运,何止倍增?
商人逐利,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之事,岂能杜绝?
若遇灾年,京师缺粮,银钱再多,可能当饭吃?
漕运之制,维系南北,其稳定关乎京城百万军民口腹,岂能轻易动摇其根本?”
杨炯字字如锥,直指杨叔方略中未曾深虑或刻意回避的深坑与隐患,“治国理财,非是纸上谈兵,更非一味求功求。需知‘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稍过,则焦糊难咽。
你之策,锐意有余,沉潜不足;见利甚明,见弊则疏。只盯着府库充盈,却未细思这充盈背后,要付出多少代价,埋下多少隐患?更未思及,如何建立一套制衡机制,防止新策滋生更大弊端?”
杨叔脸上那自信的笑容渐渐僵住,额角似有微汗渗出。他自负才学,这番筹划亦是深思熟虑,本以为能得杨炯青眼,不料却被批得体无完肤,直指其急功近利、思虑不周。
他心中不服,暗想: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些许弊端,待掌权后自可徐徐图之。
然面上却不敢显露,强自按捺下那股被轻视的愠怒与不甘,挤出恭敬之色,躬身道:“侯爷教诲的是,学生……学生虑事不周,思虑浅薄了。”
然而那低垂的眼皮下,眸光闪烁不定,手指在桌下无意识地捻着衣角,透出几分深沉与压抑。
杨炯将他的细微反应尽收眼底,心中了然。
此人才具是有,野心勃勃,亦能见事,可惜心性过于功利浮躁,做事只求效,不重根基,更缺乏对权力与利益交织下人性幽暗的深刻警惕。若放在要害位置,急于求成之下,恐非百姓之福,反易成酷吏聚敛之流。
这般想着,杨炯略一沉吟,淡淡道:“你有此心,亦算难得。户部掌天下钱粮户籍,倒是个能施展的地方。新政条陈,户部亦是重中之重。待太学课业结束,你可寻个机会,将你方才所言,更详实些,写成条陈,递到长公主府上,陈说一二。长公主总理新政财政事务,或可一听。”
此言一出,杨叔心中先是一喜,能直达长公主天听?随即又是一沉:只是“或可一听”?且并未如汤臣般直接指派去处,只是让自己去“递条陈”?
这分明是觉得自己所言尚浅,不足以委以重任。
他强压着失落与一丝怨怼,再次躬身:“谢侯爷提点!学生定当用心撰写条陈。”
杨炯不再看他,目光转向一直沉默端坐的梁氏兄弟。此二人乃名门之后,虽家道中落,然家学渊源深厚,气质沉静,颇有古君子之风。
杨炯语气和缓了些:“伯赞、叔赞,你兄弟二人,素以学问精纯著称。于这治道,又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