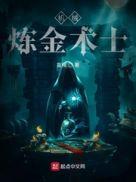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安史之乱:我为大唐改命 > 第760章 不良府改制丁娘嫁人(第3页)
第760章 不良府改制丁娘嫁人(第3页)
杜黄裳眼中闪烁着战意与振奋,袁思艺则是一贯的恭谨中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酷。
一道道命令如同离弦的致命之箭,被迅速书写、加盖玉玺,由早已等候在殿外、身着玄甲、背负加急令旗的信使接令,旋即转身,身影如鬼魅般融入殿外的沉沉黑夜,射向帝国庞大疆域的每一个角落和那神秘莫测的天工之城。
王维随着众人躬身退出大殿。当他即将跨过高高的门槛时,忍不住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眼。
裴徽依旧如同山岳般矗立在御案前。
他并未坐下,手中紧紧攥着那份仿佛还散发着血腥与硝烟气息的檄文,指节因为用力而更加分明。
摇曳的烛光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投下深刻的阴影,坚毅如万载玄铁,冷硬得不带一丝人间情感。
然而,在王维眼中,裴徽的周身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由那檄文中狂烈文字点燃的、近乎妖异的血色光晕。
那光晕既象征着无上的皇权威严与即将到来的雷霆之怒,也隐隐透着一丝被绝世凶器反噬的、令人心悸的不祥。
窗外,那沉沉如铁幕般的黑夜,似乎真的被这殿中升腾的帝王意志与檄文的杀伐之气撕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
一缕极其微弱、近乎虚幻的灰白色天光,艰难地渗透进来。
它太微弱了,不足以照亮什么,却顽强地预示着——一场席卷天地的风暴即将来临,而在风暴之后,或许是黎明,或许是…更深的血色。
殿内,只剩下烛火燃烧的噼啪声,和裴徽伫立于血色光晕中、如同战神雕像般的孤寂身影。
他手中的檄文,已然成为点燃整个帝国战火的火种。
……
……
,!
兴庆宫,偏殿。
时值深秋,晨光熹微却穿不透长安城上空沉沉的铅灰色云层。
殿内光线幽暗,几盏巨大的青铜烛台燃着明烛,火光跳跃,在悬挂于整面墙壁的巨幅舆图上投下摇曳不定的阴影。
那舆图之上,河北、中原的广袤土地,已被刺目的朱砂笔狠狠圈画,如同凝固的血痂,宣告着新的归属。
王维等人的身影消失在殿门外,脚步声渐行渐远,最终被殿外呼啸而过的秋风吞噬。
殿内重归寂静,只剩下烛芯燃烧的细微噼啪声和裴徽自己几乎不可闻的呼吸。
他并未转身,依旧背对着空旷的殿门,负手而立,如同一尊凝固的雕像,凝视着眼前巨大的舆图。
朱砂的痕迹在微光下泛着暗红的光泽,河北、中原——这片饱经战火蹂躏的土地,如今已牢牢攥在他的掌心。
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舆图上黄河的蜿蜒曲线,冰凉的丝帛触感下,是滚烫的权力脉络。
殿外空旷的回廊里,一种截然不同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打破了这片沉寂。
这脚步声沉稳有力,每一步都像是精心丈量过距离,带着长途奔袭后特有的、略微拖沓的沙砾感,靴底叩击在冰冷的金砖上,发出清晰而压迫的回响。
声音在殿门口顿住,片刻后,一个身影切入了殿内光影的交界处。
来人正是严庄。
他身材并不高大,却异常精悍,像一把收在鞘中的短刀。
一身深青色的劲装紧裹身躯,风尘仆仆,衣摆和袖口处沾着难以洗净的泥点与霜痕,长途跋涉的疲惫刻印在他微陷的眼窝和紧抿的嘴角。
然而,最令人心悸的是他那双眼睛。
狭长,锐利,眼白因缺乏睡眠而布满血丝,瞳孔却亮得惊人,如同在暗夜中搜寻猎物的鹰隼。
那目光扫过空旷大殿的每一处角落——高耸的盘龙石柱、垂落的厚重帷幕、阴影里的香炉,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审视与警惕,仿佛在确认有无潜藏的威胁。
几道浅白色的疤痕,如同扭曲的蚯蚓,从额角蜿蜒至下颌,在摇曳烛光下更显深刻狰狞——那是刀光剑影、生死搏杀留下的永恒印记。
这位曾经的伪燕宰相,安禄山最为倚重的心腹智囊,如今却成了裴徽手中最锋利、也最危险的刀,用以斩断旧主的根基。
他身上的矛盾气息令人窒息:文士的谋略与杀手的冷酷,旧朝的烙印与新主的烙印,忠诚与背叛的界限在他身上模糊不清。更令人胆寒的是,他手中紧握的,是安禄山遗留下的恐怖遗产——狼鹰卫。
那是一个深潜于帝国阴影中的庞然大物,织就的巨网覆盖刺探、暗杀、渗透、离间……是纯粹的黑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