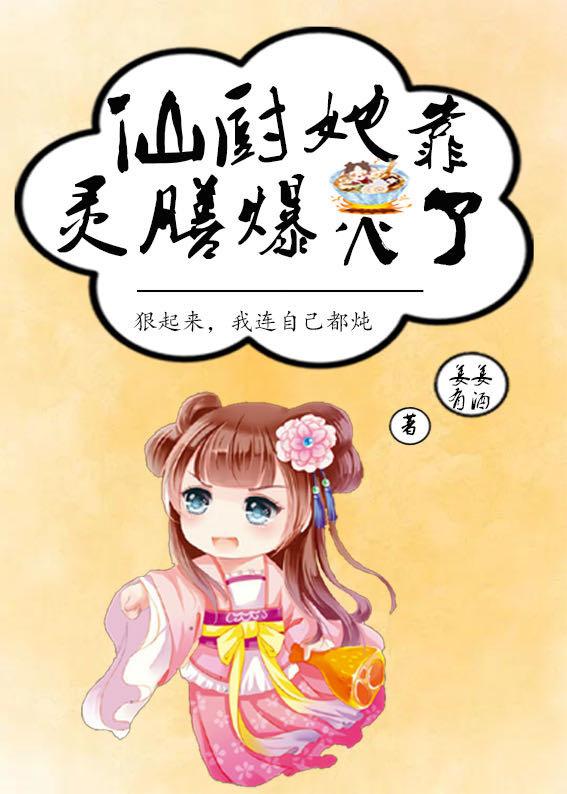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安史之乱:我为大唐改命 > 第751章 天工之城究竟是何等妖孽之地(第8页)
第751章 天工之城究竟是何等妖孽之地(第8页)
与喧嚣的讲堂一墙之隔,是一间布置雅致、焚着名贵檀香的小书斋。
紫檀木书案,官窑瓷瓶,墙上挂着名家字画。
檀香幽静,却压不住空气中弥漫的紧张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恐惧。
几个衣着华贵、用料考究的年轻士子围坐。为首者崔琰,约二十出头,面如冠玉,但此刻脸色苍白,嘴唇紧抿,眼神中带着强压的怒火和惊惶。
他博陵崔氏嫡系子弟的身份,此刻像沉重的枷锁。
崔琰猛地将手中的报纸狠狠摔在光滑的书案上,“啪”的一声脆响,溅起几滴墨汁,污染了洁白的宣纸。
崔琰(声音因极力压制而有些变调):“荒谬!无稽之谈!一派胡言!裴徽……此等奸贼,侥幸得了些奇技淫巧,立了些微末功劳,怎会有如此通天手段?一日破九郡?诛杀安禄山?掀翻七宗五姓?笑话!这定是伪造!是构陷!”
他手指用力戳着报纸上影印的密信,“这所谓的密信……这来历不明的人证画像……还有这什么‘胎记差异图解’……皆是天工之城妖术所为!是裴徽用来蛊惑人心、铲除异己的毒计!”
他试图从同伴眼中寻找支持,寻求认同。
然而,坐在他对面的范阳卢氏子弟卢敏,眼神闪烁,低头摆弄着腰间一枚价值不菲的羊脂玉佩,不敢与他对视。
旁边侥幸活下来的清河崔氏旁支崔文,更是悄悄将案头一张印有家族徽记、显然刚写好的信笺迅速团起,塞进了宽大的袖袍深处。
,!
一直沉默旁观的郑氏子弟郑玄龄,年纪稍长,约三十许。
他叹了口气,指着报纸上影印的密信,特别是那份清晰得连墨渍晕染痕迹和纸张纤维都看得见的“博陵崔氏崔弘礼致安禄山密信”影印件,苦涩地开口,声音干涩:“伪造?构陷?……琰弟,你且看看……”
他手指点在影印件右下角那个小小的朱砂印记上,“这‘弘礼私印’……这印文笔画的转折,这朱砂的色泽深浅,甚至……甚至这印角上那处细微的磕碰缺损……都与崔世伯(崔弘礼)平日常用的那方私印…分毫不差。”
他抬起头,眼中是深深的无力感,“这等影印之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神乎其技……你告诉我,如何伪造?”
郑玄龄的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崔琰强撑的气焰。
书斋内陷入一片死寂,落针可闻。
窗外寒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此刻听来如同送葬的挽歌。
崔琰的脸色由白转青,身体微微颤抖,嘴唇翕动着,却再也说不出有力的反驳。
无形的裂痕,已在这些曾经同气连枝的世家子弟心中悄然生成,并且迅速扩大为深不见底的鸿沟。
旧时代的根基,在铁证如山的影印技术面前,土崩瓦解。
一个士人低声的、带着恐惧的嘟囔打破了死寂:“那……蜀地……延王殿下……难道真的……”
没人回答,只有更深的寒意笼罩了书斋。
府衙大堂,灯火初上。
恒州刺史陈廉(已暗中投靠裴徽)端坐主位,红光满面,志得意满。堂下僚属分列两旁。
陈廉(抚掌大笑,声震屋瓦):“如何?本官早言裴殿下乃天命真龙,英武不凡!尔等昔日犹疑观望,甚至暗中讥讽本官趋炎附势,今日可服?!可服?!”
他目光如电,扫视堂下。
众僚属纷纷躬身,额头几乎触地,脸上混杂着敬畏、后怕与庆幸:“大人明察万里!高瞻远瞩!卑职等愚钝,昔日未能领会大人深意,实在惭愧!”
“殿下神威盖世,澄清寰宇,诛除国贼,实乃社稷之福,万民之幸!大人追随明主,实乃我恒州之福!”
“卑职等即刻上表,恭贺殿下扫清妖氛,正本清源!言辞务必恳切,以表我恒州军民赤诚拥戴之心!”
师爷早已铺好纸笔,饱蘸浓墨,手腕翻飞,一篇辞藻华丽、极尽谄媚之能事的贺表顷刻而成。
墨迹淋漓,透着迫不及待的效忠姿态。衙役捧着加盖了恒州大印的表章,飞跑出去,奔向驿站。
整个府衙洋溢着一种押对宝后的狂喜和急于表现的浮躁。
……
……
江南道,吴兴郡衙,黄昏。
郡衙后堂书房,门窗紧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