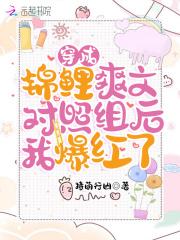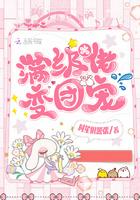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安史之乱:我为大唐改命 > 第748章 蜀地风云(第5页)
第748章 蜀地风云(第5页)
……
……
杨国忠何等精明狡诈,他深知这些蜀地豪强并非真心归附,更清楚仅靠蜀地一隅之力,绝难撼动已占据大半个北方、挟持朝廷(或另立朝廷?)的裴徽,更遑论还有那个席卷中原、如同蝗灾般吞噬一切的黄巢。
他需要外援,需要那些在中原、河北被裴徽和黄巢逼得走投无路、根基动摇却仍有巨大潜在力量和声望号召力的世家门阀——尤其是“五姓七宗”的残存力量。
这些高门大族,对“正统”的执着近乎信仰,对自身超然地位的维护更是刻入骨髓,或许能成为他撬动整个天下局面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他还需要派人与南诏和吐蕃乃至契丹人联络……
而剑南道的鲜于仲通就更不用说了。
,!
在行宫最深处一间门窗紧闭、只点着一盏如豆孤灯的密室中,气氛凝重得如同铁铸。
杨国忠亲自口述,由他最信任、心思也最为阴沉的幕僚崔景执笔。
崔景的手很稳,但笔下字迹却透着一股孤注一掷的狠劲和蛊惑人心的魔力。
信的内容极尽恳切悲情:“国事维艰,逆贼篡国,宗庙倾危,神器蒙尘!延王殿下,先帝密诏所托,正统所在,今于蜀中承天景命,然独木难支,四顾茫茫……”。
又暗含尖锐的威逼:“裴贼凶残,视士族如草芥;黄巢肆虐,所过之处,衣冠屠戮殆尽!天下板荡,非同心戮力不能存续!若坐视正统蒙尘,则天下士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以及赤裸裸的、令人心跳加速的利诱:“新朝肇基,百废待兴!待扫清寰宇,廓清环宇,凡拥立功臣,必以三公之位、膏腴之地、丹书铁券酬之!使家门显赫,百世流芳,与国同休!”。
每封信的末尾,都郑重其事地加盖上了那方新刻的“延王监国印玺”的鲜红印记,如同一个沉重的承诺,也像一个滴血的烙印。
数十名精心挑选的心腹死士,被召集到密室。
他们褪下军服或官衣,换上商旅或流民的破旧衣衫,脸上涂抹上尘土和菜色。
密封好的蜡丸被小心地藏入特制竹杖的中空夹层,或是缝进破旧棉袄的夹层,或是嵌入不起眼的货物之中。
杨国忠亲自在密室中为他们送行,目光扫过每一张或年轻或沧桑、但都写满决绝的脸。
他只给了冰冷而残酷的命令:“信在人在,信失人亡。将蜀中的‘天命’与‘希望’,送到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该送的人手中。无论付出何种代价!”
死士们无声叩首,眼神坚毅如铁。
随即,他们如同水滴汇入大海,在最深的夜色掩护下,由不同的秘密出口(废弃水道、伪装成柴房的暗门)悄然离开成都城,向着不同的方向,扑向危机四伏的中原大地。
其中一名绰号“黑鹞”的死士首领,身形瘦小精悍,目光如鹰。
在翻越城墙时,他如同壁虎般紧贴阴影,敏锐的感官让他察觉到下方暗巷中似乎有一道影子一闪而过,快得如同错觉。
他心中一凛,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升。
那影子……是野猫?还是……?任务紧急,容不得他细查,只能将这份不祥的疑虑狠狠压在心底,加速消失在城外浓墨般的夜色和起伏的山峦剪影之中。
他不知道,在他身影消失后,暗巷的阴影里,一个同样融入黑暗的身影悄然显出身形,对着他消失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随即也无声地隐去。
……
信使们的身影,如同投入怒海的小舟,消失在蜀道的崇山峻岭与中原的烽烟之中。
成都城内,杨国忠营造的“王业复兴”景象依旧喧嚣鼎沸。
军队在尘土飞扬中操练,口号震天;工匠在炉火旁挥汗如雨,打造着兵器甲胄;官员们在“监国行辕”中进进出出,捧着文书,步履匆匆。
但这虚假的繁荣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宫殿,根基摇摇欲坠,每一份热闹都透着一股竭尽全力的虚张声势。
行宫里,那位木偶般的“延王”李玢,在又一次如同酷刑般的“接见”了几位前来表忠心的官员后,身心俱疲地瘫坐在那张冰冷坚硬的“龙椅”上。
宽大的袍袖滑落,露出手腕上几道被绳索捆绑留下的、尚未完全消退的青紫淤痕,那是前几日他试图反抗、不愿配合“演戏”时留下的印记。
烛泪缓缓堆积,如同他心中凝固的绝望。
而在锦江王氏的深宅深处,王嵩独自一人跪在供奉着列祖列宗牌位的祠堂里。
檀香袅袅,他恭敬地上了三炷香,低声祷祝:“列祖列宗在上,不肖子孙王嵩,为保家族基业,行此险招……望祖宗庇佑,使我王氏于乱世中,得窥登天之路……亦或……保全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