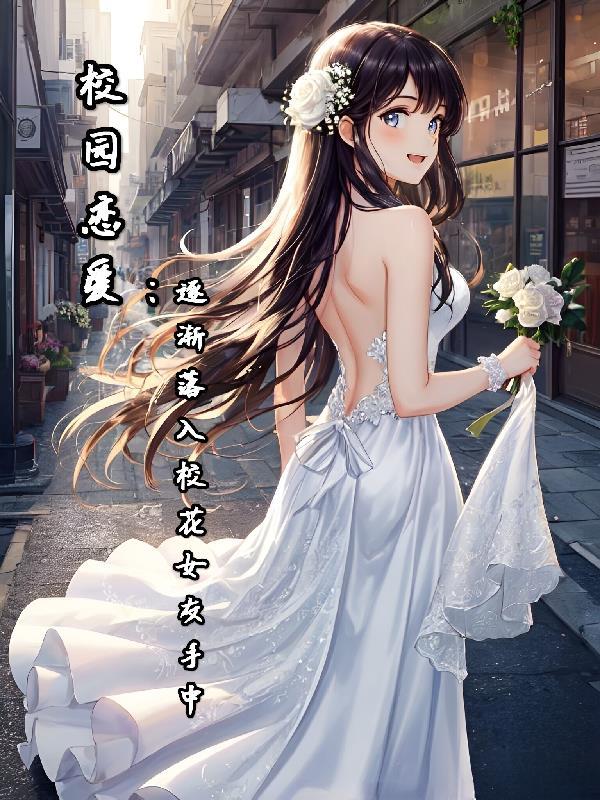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女驸马但误标记太后 > 90100(第16页)
90100(第16页)
她也学着慕兰时的语气拖长语调,“娘娘的脸皮,到底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厚的。”
“慕大人彼时是不是这么说的?”戚映珠忽然加重语气,侧过头用余光斜睨了慕兰时一眼,“哀家也想知道,慕大人这般厚的脸皮,又是从什么时候变来的?”
——哪有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女人!
她居然还口口声声地说“娘娘不认识兰时的字”!戚映珠从来没告诉过慕兰时,她看了她多少字。
……当然,也可以推理得出。
毕竟不见天光、酸涩弥漫的暗恋,总得靠着一件又一件有关于她的物件,才能长久地保持感受。
戚映珠怅然了一瞬。
她当然认识慕兰时的字,她太熟悉她的笔锋。
前世隔着一道珠帘,她看不真切她的容颜。她只能从她呈上来的奏折窥见一二。
曾在无数个辗转反复的日夜,她一遍又一遍地看她洋洋洒洒上书的奏文。
看它的顿挫、看它的横折、看它的竖钩——
这样锋锐清丽的字迹,在无数个夤夜啃噬她的梦境,就像太庙香炉里燃不尽的香与灯火,生生地将“克己复礼”四个字烙进骨髓。
见字如见人,她的字,堪称顽固,
慕兰时顽固的字也像她本人的为人一样。
顽固地,存在于戚映珠顽固的记忆里面。
她早就把慕兰时所写的横平竖直刻进自己的记忆,并顽固地不肯消除。
“怎么不说话?慕大人只准自己问,便不准别的人问了?”思及此,又听不见慕兰时的回应,心头憋闷着的一股子气顿时又爬了上来,
就是不要脸!
“娘娘不是别人。”慕兰时忽答。
戚映珠又是一噎。
这真是答非所问!难道这样就能哄得她开心了么?
好吧,一瞬之间戚映珠也不得不承认此事。
她咳嗽了一声,“我问你的脸皮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厚的,不是让你挑我话里错的!那我换句话问。”
“问什么?”
“慕大人还当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问了,便不让我问。”她说得直白,这回也不给慕兰时乱说话的余地。
慕兰时果然挫败地低头,蹭了蹭戚映珠的脖颈,又嗅了嗅她脖颈间的香气,说道:“兰时什么时候这么霸道了?明明是娘娘误以为这东西是兰时的手笔,却不能让兰时委屈一下?”
倒是同她讲不明白。
戚映珠泄气了,摇摇头,终于将话题拉回正题:“既然不是慕大人写的,这东西是谁的?”
“娘娘莫非看不出来?”
戚映珠再度沉默了。
“……看得出来,”她缓缓地说,脸上的潮。红都因着眼前的事实冲击而减弱几分,“但是,这东西是他所写?”
这些淫。词。秽。语,戚映珠当然不能将这字同那个高风亮节、以世家清流之首自居的人身上!
“不然呢?”慕兰时笑意愈发深重,呼出来的热气也喷洒着嘲讽,“如果不是他写的,兰时也不会费尽心机命人取来了……”
戚映珠尚不可思议。
“梁大人单独卖自己的墨宝还不够,私底下或许是觉着,披着这一张‘清流名臣’的假面太过恼人,百般压抑之下,只能用这样的手段发泄了?”慕兰时若有所思地说着。
戚映珠脑袋转得很快,她也想明白了个中关窍。
梁识正在借由“沧州矿脉”一案打压慕兰时——这事当然不能对慕兰时直接造成什么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如有波连,她的仕途受阻定然不可避免。
而慕兰时嘛……
“不愧是慕大人,倒是深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道理。”戚映珠低声道,放下了手中的纸册。
她的心里,又想起上次慕兰时的疑惑——她问她,难道就要这么放过徐沅和戚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