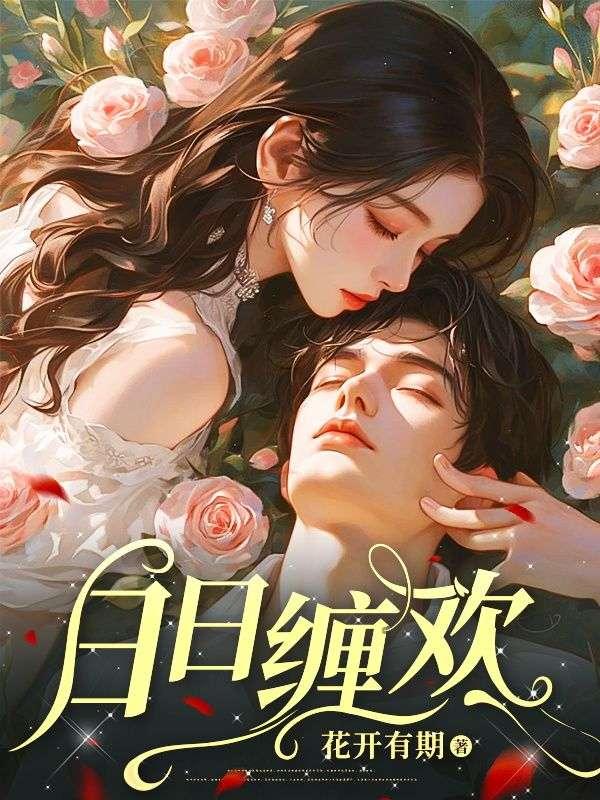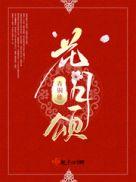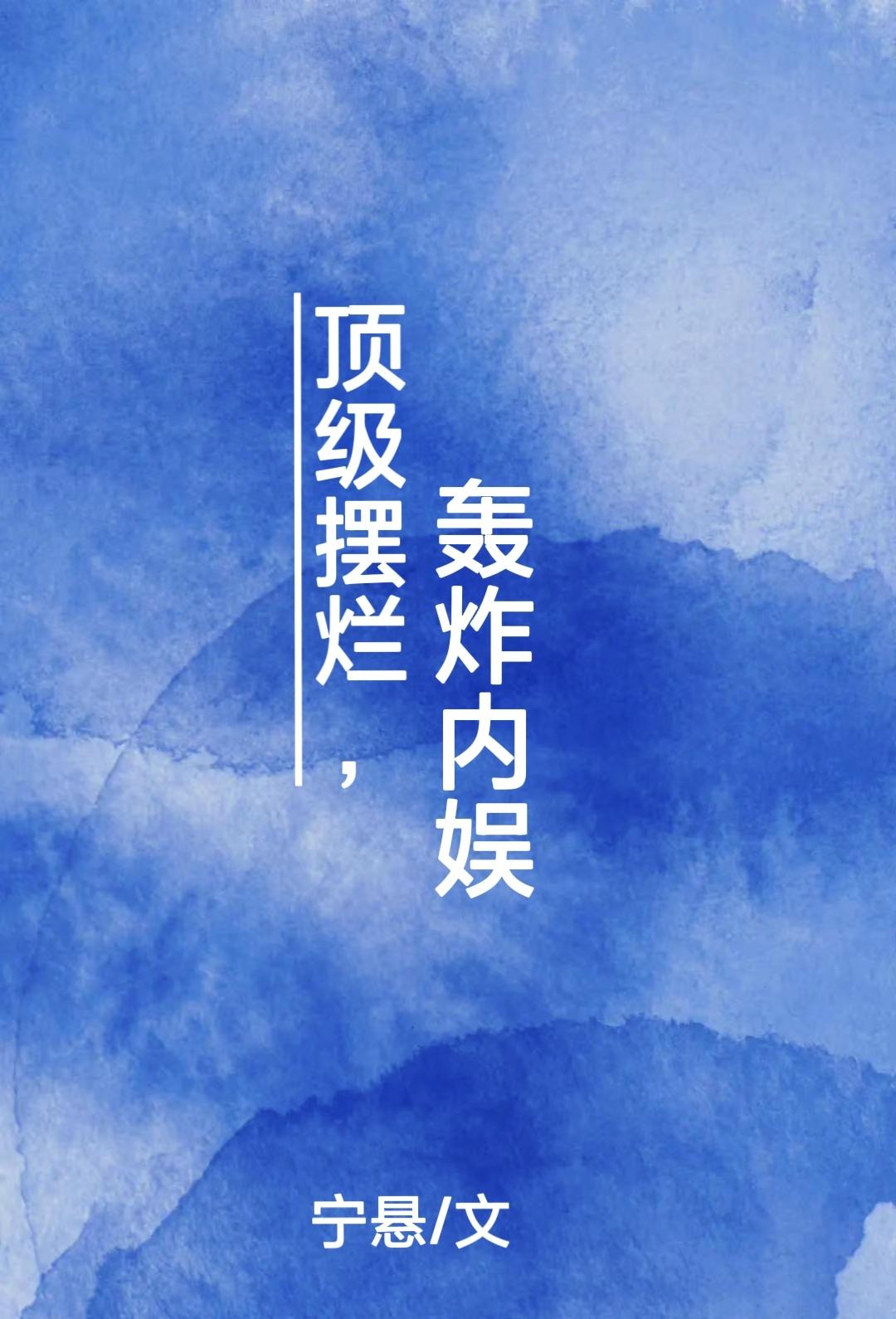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塞音老仙闹大明 > 第276章 火爆的塞瓦贸易(第2页)
第276章 火爆的塞瓦贸易(第2页)
最奇怪的是一群穿白袍子的,这些人不卖货。而是给蒙古牧民免费瞧病,还给送药。
主要针对的是发热的病人,和那些腹部臌胀的小孩。
这些白袍子会给病人咯吱窝下面夹一根玻璃棒(体温计),然后煞有介事地在本本上记录。
不过药片也不是白给的,必须当场服用,回头还要给白袍子说明诊治效果。
这是姜王后的慈善基金会派遣的医疗队,一是向草原传播卫生知识,二是与底层民众建立情感联系。
下一步自然就是传播塞音教了。
草原人对外来宗教接受程度较高,佛教、伊斯兰教他们都信,为啥不能信塞音教?
等他们都信了塞音教,那么这块地方还不是早晚要到塞国的碗里来?
交易进行了几天,便有瓦剌商人闻讯赶到了。
阿拉知台就是瓦剌的大商人,他的商队光是驮马就有几百匹,伙计们都配有刀枪。
草原上消息散布的很快,阿拉知台的商队得到信就开始准备了,这么大的商队需要备货,能这么快赶到巴里坤贸易点,可见此人的组织能力是相当强的。
作为大商人,阿拉知台对塞国许多商品并不陌生,但长期以来,塞瓦贸易被卖卖回回从中间插了一杠子,阿拉知台拿不到一手货源,就只能做“二批”(二级批发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做过贸易的朋友都知道,在信息发达的后世,中间商每多一级,利润就要差5个点左右。
这是在明朝,消息闭塞,交通不畅,战争频繁,这种利润差会被放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塞国人明码标价做生意,但他只要把货物转运到各部落,定价权自然就在自己手上。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阿拉知台心中产生。
他和塞国大大小小的商人聊了一圈,最后把目光瞄上了一个人。
“胡老哥,你能搞到卡车不?”
“能,咋不能呢?前两年兴许难一些,不过今年嘛,嘿嘿。”
被称为胡老哥的商人示意阿拉知台附耳过来,低声说道:“今年军部淘汰了一批卡车,虽然是二手的,可是价格便宜。也就我在军部有人,其他人可拿不到。”
胡老哥正是关陇商贸的掌柜胡宽。按说他这种大商人也该养尊处优,但此时塞国整体精神风貌是积极向上,各家大掌柜都是冲在第一线的。
对于草原这块新市场,胡宽还是相当重视的,所以这趟亲自跑来了。
阿拉知台大喜过望,他以商人敏锐的直接,一下就看出未来物流才是贸易的关键所在。
“我打算在瓦剌各部建立小贸易点,嗯,搞成土围子就成,先搞上十个看看情况。我想找家有实力的商号合作,要是胡老哥有兴趣,以后我阿拉知台就只认关陇商贸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正是阿拉知台率先搞定居式商业模式,在草原上引起轰动。以至于引发了一系列变化,对牧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塞瓦两国有了巴里坤的贸易口岸,他的思维随着形势转变,路上就有了搞“分贸易点”的想法雏形。
这也是需要有相应的实力支撑的。
“自无不可!”
胡宽与阿拉知台一拍即合,做生意选择合作伙伴,抢占先机非常重要。
例如后世国外4S店、连锁超市进入国内,别看他实力多么雄厚,一样需要与本地经销商合作,否则根本寸步难行。
巴里坤的贸易虽热,但也只是在草原的一隅悄然演变。
远在万里的大明京师,皇上朱棣得知了塞瓦两国的PY交易,顿时怒不可遏:
“娘的!朕苦哈哈地跟瓦剌人干仗,他姓刘的悄默声地就把果子摘了,真是岂有此理!”
原本历史上,马哈木战败后,次年便向大明献上降表,重新臣服。可如今瓦剌却成了塞国的小弟,这叫朱棣如何能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