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塞音老仙闹大明 > 第261章 罚单(第1页)
第261章 罚单(第1页)
说话间,就到了来年正月(塞音二十二年,大明永乐十一年)。这天是正月初五,民间称为破五,家家户户燃放爆竹,炸的噼噼啪啪作响。
陇西漳县,盐川庄外匆匆忙忙跑来一人,穿着件宽大无比的棉袄,将整个人包的严实。
村民还是有人认出来人,冲那人喊道:“彭全,你日急慌忙的,是给老子送钱来么?”
彭全是汪府豢养的狗腿帮闲,时常跟村里人耍两手钱,故那闲汉有此一问。
彭全脚下一个趔趄,在雪地里打了滚,口里喊了两声“麻达(麻烦、糟糕之意)了!麻达了!”爬起来就跑,对闲汉的调侃全然不理会。
到了汪府,跟门子知会一声,彭全等了半晌才过来个三等管家。
“不得了了,县城里头来了官军,见铺子就贴封条,见闲人就抓。牛大、黑娃、皮家兄弟都给绑走了……”
事情紧急,彭全一把抓住管家的丝绸衣袖,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哎!真是鸡蛋碰石头!”
管家是个晓事的,气得直跺脚,终于色变。
消息一层层报了上去,中枢之人还四平八稳,下边已经全乱套了。
陇西汪氏可以说是陇西最大的豪强,没有之一。其祖上汪世显本是金人,属蒙古汪古部。
后来投降蒙元,曾经做过巩昌府(塞国改为陇西府)便宜都总帅,统领秦州、巩州二十余州府,几乎等于陇西小诸侯,死后追封陇西公。
到如今,汪家已经在陇西差不多二百年,这么长时间开枝散叶,汪家人遍布陇西各县,就连秦州,陇南府的成县等地都有汪氏后人。
改朝换代后,汪家先是投降大明,又降塞国,实力已经大大被削弱。
可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汪家长房的汪钊一直在军中,如今担任塞军守备军的营长,只可惜被调去了南边。
而当家的汪庸、汪寿兄弟,更是垄断盐川的盐矿,趁会宁办股市那会的东风,把盐川盐业运作成上市公司。
可谓是权也有、钱也有。
汪庸虽然担任过总山合议会的议员,可他家始终与总山保持距离,不冷也不热。
这样的豪强多了去了,例如红谷川的王西宝,关西七卫,四川、云南的土司等等。像奢香夫人那样,积极要求进步的头人(豪强)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朝廷和地方豪强之间,始终横亘着一根刺,那就是土地问题。
这个问题因为塞国的领地扩张而被弱化了,但一直存在。一方面,塞国宪法要保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工业化发展也需要大量土地作为生产资料。
但豪强手中掌握着大量土地,就比如汪家,他家的地没有红谷川王家多,但手里的水浇地也有十几万亩。
刘学勤不想搞打土豪、分田地那种破而后立,就只能采取温和的赎买办法。但涉及到公共事业的部分,有些事就不好商量。
比如修桥、铺路、架设电线桩等等,你要占人家的私田,这些人要么漫天要价,要么暗戳戳地搞破坏。
地方官员气急了,就恨不得拔刀子。
要不是总山一直保持克制,那必然会导致流血事件。
这就是刘学勤送给太子朱高炽【妥协】的深意,憋屈不?那是自然。可是暴力手段一旦放下去,造成的结果可能十倍、百倍放大。
可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老汪家得到消息,也着实惴惴不安。
初六,汪庸兄弟就串联了当地几大家族,李家、边家、米家等,因为陇西罢工事件已经被官府定性为“民乱”,往大了说,那就等同造反。
商量了一天,大伙儿也没议出个所以然来。倒是有人提出去台湾投奔粟登科,可是他们家大业大,那么多财产也不是一下就能变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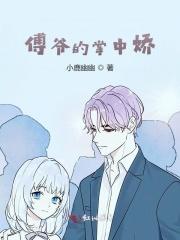

![女道君[古穿今]](/img/648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