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 585谁坑谁(第1页)
585谁坑谁(第1页)
赵振国一路将刘黑豆和自家大哥送到了招待所外头。
眼瞅着四周静悄悄的,连个过路的人影都没有,大哥那憋了一路的好奇心,终于像开了闸的洪水,再也按捺不住了。
大哥猛地一拍赵振国的肩膀,那力道震得赵振国肩膀微微发麻,只听大哥扯着嗓子,带着几分急切又带着几分埋怨地问道:
“小四啊,这到底咋回事儿哟?你是不是给我拍电报说到这边出差么?咋又成去港岛了?”
刘黑豆也出言附和道:“对啊,我是收了人家的定金说要送三个。。。。。。
巡演的第十九站,他们来到了西藏昌都地区的一座藏族村落。这里海拔较高,空气稀薄,阳光明媚却带着刺骨的寒意。村庄依山而建,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一条清澈的溪流从村中蜿蜒而过,滋养着这片土地。村口立着一座玛尼堆,五彩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信仰与传承。
晨曦和林强刚下车,就被一位身穿藏袍的中年男子迎上前来。他名叫扎西,是村里的文化干事,皮肤黝黑,眼神深邃而坚定。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村。”扎西用略显生硬的普通话说道,“这里的人,世代信佛,生活简单,但也孤独。”
林强笑道:“我们不是来表演的,而是来倾听和陪伴的。”
他们跟着扎西走进村寨,见到了村里的老人们。他们坐在寺庙前的石阶上,或捻着佛珠,或低声诵经,神情安详。晨曦蹲下身,轻声问一位年迈的老奶奶:“您还记得小时候跳舞的样子吗?”
老奶奶微微一笑,眼神中透出一丝怀念:“小时候,我们围着篝火跳锅庄,那是最开心的时光。”
晨曦沉思片刻,回头看向林强:“我们要编一支舞,叫《锅庄情》。”
林强点头:“用经幡为舞衣,用山风为节拍,让老人与孩子一起跳。”
课程开始的第一天,依旧冷清。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晨曦和林强没有气馁,而是带着志愿者们走进家家户户,邀请他们来学舞。
他们在一户人家前停下,屋前晾晒着几件藏族刺绣,屋后是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一位姓次仁的老人坐在门前,手里拿着一根木雕的转经筒。
“我年轻时,每天都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寺庙诵经。”次仁爷爷声音沙哑,“现在腿脚不便,只能坐在这里,看孩子们跑来跑去。”
晨曦蹲下身,轻声说:“您愿意和我们一起跳一支舞吗?用您的转经筒,跳一支属于您的舞。”
次仁爷爷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头:“好,我试试。”
晨曦为他编了一支舞,名叫《转经情》。舞蹈动作简单,却充满温情:老人手持转经筒,象征着一生的信仰与坚守,孩子从远处跑来,接过转经筒,继续前行,两人相视一笑,紧紧相拥。
次仁爷爷跳完,眼角湿润:“原来,我还记得怎么跳。”
“您不只是记得怎么跳,”晨曦轻声说,“您还在用舞步,告诉孩子,您这一生,从未放弃信仰。”
第二天,课程报名人数翻了一倍。第三天,整个文化广场都被挤满了。
晨曦和林强趁热打铁,开始组织小型汇报演出。他们鼓励老人们写下想对孩子说的话,再将这些话语编入舞蹈中,用动作表达出来。
“我以前觉得,我这一生就这样了。”一位姓达瓦的老人在课堂上说,“孩子们都走了,我也老了,没什么可期待的。可你们来了,带着舞蹈,带着爱,让我重新找回了活着的意义。”
她的儿子在拉萨打工,已经三年没回家。可当她跳完那支专门为母子设计的舞蹈《锅庄情》后,儿子竟然主动打来了视频电话。
“妈,我看到你跳舞了。”儿子在电话里哽咽,“你跳得真好。”
达瓦奶奶眼眶红了,却笑着点头:“你也要学,下次回家,我们一起跳。”
演出当天,晨曦和林强站在后台,看着台上那些原本沉默寡言的老人,如今牵着子女的手,跳着他们教的舞,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你看,”晨曦轻声说,“沉默也能被舞步打破。”
林强握住她的手:“是啊,只要有人愿意迈出第一步,爱就会重新流动。”
演出结束后,他们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写信的是一位独居老人,信纸有些泛黄,字迹略显颤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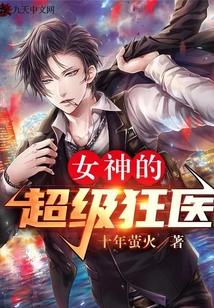

![[红楼]林如海贾敏重生了!](/img/3124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