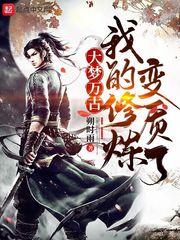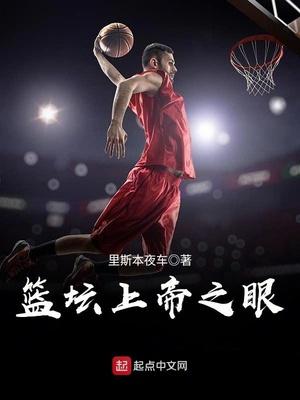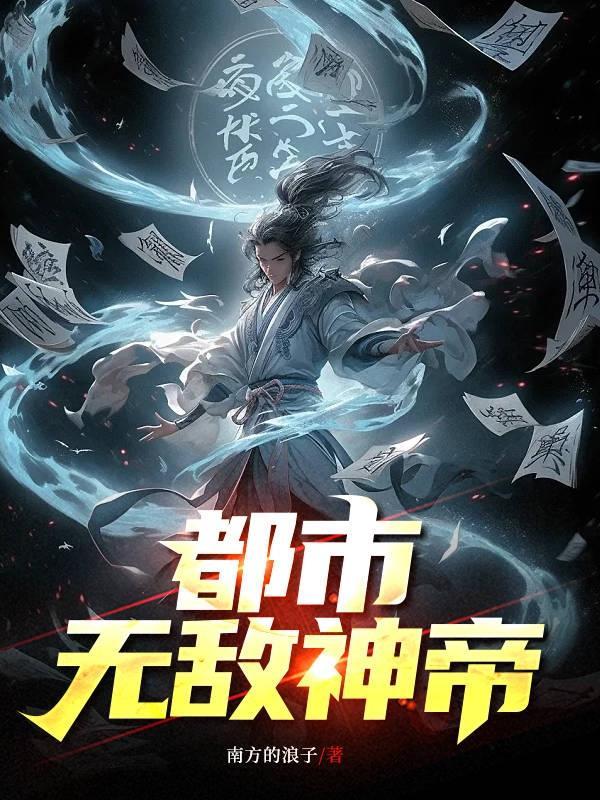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官婿美人香 > 第635章 专项审计(第1页)
第635章 专项审计(第1页)
郑国涛亲自拿着文件来找向南,脸上依旧是那副沉稳中带着诚恳的表情:“向书记,您的指示,我们政府班子绝对拥护!这管网改造,利县利民,大好事!”
跟着,郑国涛话锋一转,眉头恰到好处地拧起:“不过,现实困难确实摆在眼前。财政压力太大,几个口子都等着钱救急。您看……是不是步子稍微缓一缓?或者,我们先搞个试点?集中力量啃一小块硬骨头,做出个样板来?这样既能回应您的关切,也能给上面和群众一个看得见的交代,压力也小些。”
他言辞恳切,分析利弊,一副完全从工作出发、为向南着想的姿态。他甚至主动提到了“试点样板”,仿佛这已经是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和全力支持。
向南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上那份《紧急通知》的复印件。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过了许久,久到郑国涛脸上的诚恳都快要挂不住时,向南才缓缓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似乎是妥协的疲惫,又像是无奈的理解。他轻轻叹了口气,声音低沉:
“郑县长是老颍阳,情况比我熟,困难也看得比我透。你说得对,一口吃不成胖子。那就……先搞试点吧。选一个隐患最突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片区,集中力量,务必打造成一个标杆工程。钱的问题……”他顿了顿,目光看向窗外,“政府这边克服一下,优先保障试点。至于后续……等试点有了成效,我们再想办法。”
郑国涛眼中瞬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亮光,那是一种猎物终于踏入预设陷阱的满意。他立刻挺直了腰板,声音洪亮了几分:“请向书记放心!试点工作,我亲自抓!一定打造成精品工程、民心工程!绝对不给您丢脸!”他拍着胸脯,信誓旦旦,仿佛之前的种种困难,在他亲自出马下都将迎刃而解。
试点工程在紧邻老县委家属院的低洼片区“柳树巷”轰轰烈烈地启动了。挖掘机轰鸣,围挡竖起,写着“民生工程功在千秋”的红色横幅在风中猎猎作响。郑国涛几乎每天都要去工地转一圈,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困难”,接受县电视台的采访。他意气风发,声音洪亮地向镜头描绘着工程完工后的美好图景。工地的尘土似乎都沾染上了他志得意满的气息。
“民心工程”的代价是巨大的噪音、出行的不便和施工初期不可避免的扬尘。老家属院里怨声载道,县里几个主要的本地网络论坛上,也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劳民伤财”、“面子工程”、“新官上任三把火,烧的是老百姓的安宁”……这些声音不大,却像细小的砂砾,悄悄磨损着向南作为新任书记的民意基础。
向南的办公室依旧安静。他案头堆放的文件里,关于柳树巷试点的进展报告只是其中寻常的一份。他看得更多的,是县审计局每季度例行报送的《财政收支审计综合报告》,以及一些看似与当前工作毫不相干的资料——几份关于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历年调整对比文件,一些土地招拍挂公告的存根复印件,甚至还有几份企业信用查询报告。
他看得很慢,很仔细,用不同颜色的笔在上面做着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标记。有时,他会拿起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打给一些不在颍阳本地、却拥有专业权威的部门,咨询着一些非常具体的政策界定问题或操作流程。电话那头的声音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向南只是静静地听,偶尔“嗯”一声,脸上的表情如同深潭。
时间在柳树巷工地的喧嚣和向南办公室的沉寂中悄然滑过。年后的第一场寒潮裹挟着冷雨侵袭颍阳时,县委常委会再次召开。议题一项项进行,波澜不惊。郑国涛主导的几项工作进展顺利,他汇报时语气沉稳,带着一种胜券在握的从容。会议接近尾声,气氛松弛下来。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倾听的向南,从面前一摞文件中,抽出了一份薄薄的、封面印着审计局红头的材料。他轻轻推到会议桌中央,动作平稳,却让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
“各位同志。”向南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冰投入温吞的水中,瞬间驱散了那点松弛的氛围,“在审议下一项议题前,有份材料,请大家先过目一下。这是审计局日常工作中发现的一些线索摘要,涉及开发区部分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使用,存在一些……不太清晰、不太规范的地方。”
会议室里的空气骤然凝固。
郑国涛脸上的从容瞬间僵住,如同面具出现了一丝裂痕。他旁边的常务副县长猛地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瞪得溜圆。几个郑系常委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脸上血色褪去。
向南的目光平静地扫过众人,最后落在郑国涛脸上。他的眼神里没有任何攻击性,甚至带着一丝例行公事的平淡:“数额不算特别巨大,但性质敏感,关系到开发区的健康发展和政府公信力。为了彻底查清问题,厘清责任,同时也为了保护干部,避免不必要的猜疑,我个人建议——”他刻意停顿了一下,清晰地吐出每一个字,“——由县委向市里打报告,申请派出专项审计工作组,进驻开发区,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审计核查。把问题查清楚,该规范的规范,该澄清的澄清。郑县长,你看呢?”
死寂。比第一次常委会上向南提出管网改造时更甚。空气沉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空调的“嗡嗡”声成了唯一的背景音,此刻听来却无比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