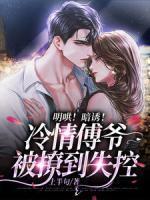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官婿美人香 > 第632章 迎头一棒(第1页)
第632章 迎头一棒(第1页)
向南没想到的是,在家里有多轻松,来颍阳就有多压抑。
到颍阳的头一天,向南就知道自己坐进了一张无形的网中,他必须要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雨。
年初九,也是向南正式上任的第二天。
县委大楼的走廊宽阔得能跑马,新刷的墙漆泛着刺鼻的冷光。
向南推开那扇挂着“县委书记”铜牌的厚重木门,办公室很大,却空得能听见回音。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几把皮椅,一组待客沙发,除此之外,连盆像样的绿植都没有。前任走得仓促,似乎连一丝可供凭吊的气息都吝于留下,只留下这刻意营造的、近乎荒凉的整洁。
窗外的天空阴沉得如同浸了水的铅块,云层低低压在青灰色的建筑群顶上,似乎在酝酿着一场蓄势待发的风暴。空气又干又冷,吹在皮肤上,让人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意。
办公桌上孤零零地躺着一份文件。
向南的指尖拂过冰冷的桌面,拿起那份薄薄的《关于调整县委县政府分工的通知(建议稿)》。落款是县政府办公室,鲜红的公章盖得端正无比。他逐字逐句地看下去,嘴角那点初来乍到、礼貌性的弧度一点点被熨平了。
建议稿写得滴水不漏,条理清晰。
向南这个新任一把手“负责县委全面工作”,而下面,林林总总的关键领域——核心经济、政法维稳、项目考核……那些真正沉甸甸、能撬动局面的实权,赫然列在县长郑国涛的名下。文件末尾那行“妥否,请向书记阅示”的小字,带着一种精心包装过的试探和不容置疑的强势,刺眼得很。
向南把文件轻轻放回桌面,纸张落在光洁的红木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在过分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
他踱到窗边,目光投向楼下。
县政府那边的小楼前,一辆黑色的奥迪A6L正稳稳停下。车门打开,一个身材敦实、穿着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利落地钻了出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油亮整齐。他站定,微微仰头,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县委大楼这排窗户。
隔着好几层楼的距离和厚重的玻璃,向南看不清他的表情,却清晰地感受到那道视线沉甸甸的分量——带着审视,带着了然,也带着一种久居其位的、不容挑战的笃定。
县长郑国涛。
这个名字,连同他身后那张盘根错节、覆盖颍阳每一个角落的网,在向南上任前的无数份“情况参考”里,早已被勾勒得轮廓分明。
桌上的电话猛地炸响,铃声尖锐地撕破了死寂。向南回身,拿起听筒。
“向书记,您好您好!”话筒里传来一个热情洋溢、中气十足的声音,洪亮得几乎不需要扩音,“我是郑国涛啊!实在不好意思,县里临时有个急事,耽误了去迎接您,失礼失礼!您看,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开个常委会?一来呢,给您汇报汇报县里的基本情况,二来呢,也让大家伙都认识认识我们颍阳的新班长嘛!”
郑国涛的声音里透着熟稔的亲切,仿佛只是老友间的一次寻常约定,听不出丝毫文件上那份建议稿的刀光剑影。
“好的,郑县长,就按你安排的来。”向南的声音平稳得像一泓深潭,不起波澜。他挂断电话,办公室里重新陷入那种空旷的寂静,只有窗外天空的铅灰色,似乎又浓重了几分。
下午三点整,县委小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擦得锃亮,倒映着头顶惨白的灯光。常委们陆陆续续进来,彼此点头,低声寒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向南在主位坐下,目光平静地扫过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那些在资料照片上看过无数次的人,此刻真实地坐在他面前。他们的眼神掠过他时,大多带着一种谨慎的、短暂的接触,随即飞快地垂下,或者移开,投向坐在向南左手边第一个郑国涛的位置。
郑国涛最后一个进来,步履稳健,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一边走一边向几位常委点头致意,那份熟稔与从容,仿佛他才是这间会议室真正的主人。他走到向南旁边,伸出手:“向书记,都齐了,您看……”
向南微微颔首。
会议开始。
郑国涛率先发言,声音洪亮,条理清晰。他如数家珍般汇报着颍阳的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串串漂亮的数据从他口中流畅地吐出,像一串串被精心打磨过的珍珠。他谈笑风生,偶尔插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引得几位常委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气氛看似融洽而热烈。
轮到向南讲话。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感谢郑县长和各位同事的介绍。我刚来,情况还不熟悉,主要是学习、调研。下一步,想重点围绕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深入基层,摸清实情;二是抓牢党建,强化组织保障;三是……”
向南顿了顿,目光再次扫过全场,:“尤其要关。注民生短板,比如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老旧管网问题,存在安全隐患,必须提上日程,尽快研究解决。”
他特意点到了“老旧管网”这四个字,话音落下的瞬间,会议室里那层看似融洽的热闹气泡仿佛被无形的针戳破了。
刚才还在郑国涛玩笑下微笑的几位常委,此刻脸上的笑容像是被冻结了。他们有的低头盯着面前的笔记本,仿佛上面突然开出了奇异的花;有的端起茶杯,专注地吹着水面根本不存在的浮沫;有的则把目光投向郑国涛,那眼神里带着请示,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死寂。只有空调出风口单调的“嗡嗡”声在房间里固执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