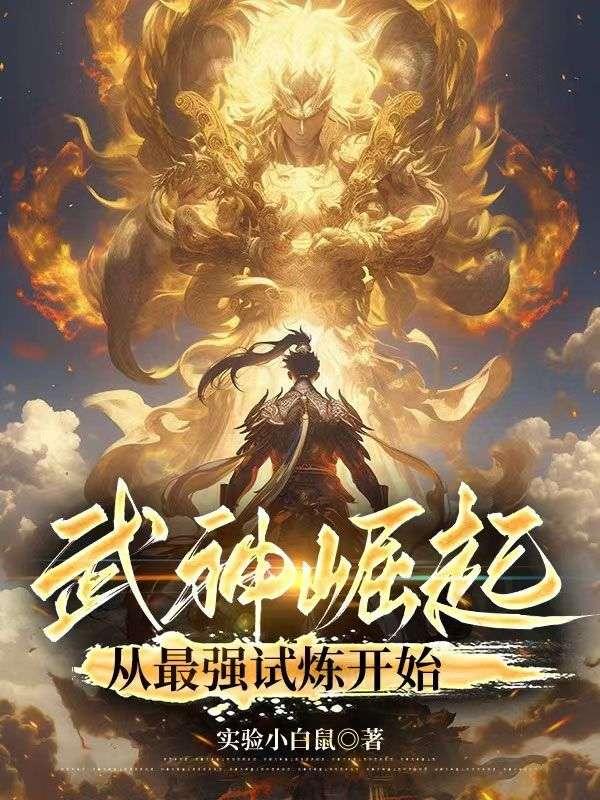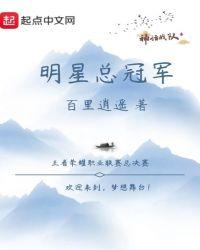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暖暖而生 > 第232章 擦肩而过(第2页)
第232章 擦肩而过(第2页)
陈行宁温和地婉拒了“诸位乡亲厚爱,行宁铭感五内。然江南情势叵测,此去凶险难料,岂能带乡亲们涉险?再者,”他顿了顿“江南一事还需阿暖安排,且我此行队伍已然不小,若再添人,恐过于招摇,于行程、于安全皆非上策。”他言辞恳切,没有半分新贵骄矜,仿佛还是当年那个温和的村学先生。
村民们虽失望,却也理解,更感念他的坦诚与不忘本。
队伍中的秦云飞,也抽空回了趟家,得知妻儿已随一丰回江南,秦乐也追去了,索性我只能忧在心间。
在广丰县停留了五日,处理完各项事务,陈行宁便率队继续南下。
四月十六日,行至合安县境,远远便望见旌旗招展,一队更为庞大的车马仪仗停在官道驿站旁——正是赴任江南东道提督的卢清哲一行。
卢清哲身着绯色官袍,气度沉凝威严。他的护卫皆是精锐,甲胄鲜明,远非陈行宁的队伍可比。
提督之位,统辖一道军政,仅在刺史之下,实为封疆大吏,足见康圣帝对其的倚重与赋予的平乱重任。
此番在合安,卢清哲便是要先行接见所有赴任江南东道的官员,统一部署。
陈行宁肃整衣冠,上前恭敬拜谒,两人在驿站内密谈良久,卢清哲神色严峻,将江南一些情况告知,并面授机宜。
陈行宁凝神静听,心头愈发沉重,事态紧急,他不敢耽搁,次日清晨便向卢清哲辞行,率队先行渡江。
大江横亘,烟波浩渺,渡船破开浑浊的江水,缓缓驶向对岸。
陈行宁独立船头,扶着冰冷的木质栏杆,任凭江风吹拂起他的衣袂。他极目远眺,那片被薄雾笼罩的土地,便是阿暖无数次向他描绘过的江南了。
“阿暖说,江南很美,诗情画意……”他低声自语,眼前仿佛浮现出阿暖笑语嫣然的模样,说着小桥流水、烟雨楼台、十里荷花。
但此刻映入他眼帘的,除了春日应有的葱茏水色,似乎还隐隐笼罩着一股沉寂之感。
对岸的轮廓在雾气中逐渐清晰,岸边的垂柳依旧袅娜,偶有水鸟掠过江面,留下一串涟漪,诗情画意犹在,只是留恋景致的人少了。
陈行宁的手,探了探晨间江上的薄雾,那冰冷的触感,提醒着他此行的使命,江南的“美”,正等待着他们去驱散阴霾,重新擦亮。
船,靠岸了。
陈行宁扶着渡船栏杆,心潮起伏地踏上江南土地时,他全然不知,就在昨日,他魂牵梦绕的阿暖,正带着林家的亲眷,悄然登上了北去的客船。
两支队伍,一支代表着朝廷新锐南下赴任,一支承载着丧亲之痛北归故里,虽同处一县,却如同两条短暂交汇又迅速分离的溪流,在喧闹的官驿码头擦肩而过,未曾照面。
陈行宁南渡,心念江南的阿暖;林暖北行,亦不知心心念念的陈先生已近在咫尺,这阴差阳错的错过……
三日后,风尘仆仆的陈行宁一行抵达广丰县城北门。
远远便见城门处旌旗微展,数位身着官袍之人已在等候。为首一人,年约四旬,面容儒雅,蓄着精心打理的美髯,正是即将离任的越州县县令祝长青,他身侧是同样即将高升的卢光,以及张县丞、吴县尉等一干僚属。
陈行宁连忙下马,快步上前,躬身行礼:“下官陈行宁,见过祝大人、卢大人及诸位同僚。”
祝长青朗声一笑,上前虚扶,眼中满是长辈看子侄般的欣赏:“快快免礼!早听小暖那丫头念叨了多少回,言其未婚夫婿陈知远如何光风霁月,才学过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仪表堂堂,气度沉稳!”他语气热络,毫不掩饰对陈行宁的好感。
卢光也含笑点头,目光温和中带着期许。
陈行宁恭敬道:“大人谬赞,行宁愧不敢当。”
“欸!”祝长青一摆手,佯作不悦“贤侄此言差矣!你与小暖既有婚约,我托大,你当唤我一声‘祝世叔’才是正理!”他指了指卢光,“至于卢大人,更是小暖的义父,自然也是你的义父,自家人面前,何必拘泥官场俗礼?”
卢光也笑着接口:“正是此理。知远,往后私下里,便唤我义父即可。”
感受到两位的善意,陈行宁也不拘谨再次郑重行礼:“是!小侄见过祝世叔,见过义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