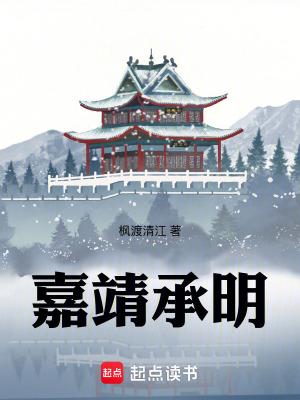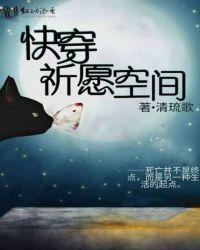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暖暖而生 > 第227章 归处是心安(第2页)
第227章 归处是心安(第2页)
瘟疫初起时,恰逢凛冬,那最初的几声咳嗽、几场高热,被轻易地归咎于冬日寻常的“寒症”。
医馆药铺里,坐堂的大夫们捻着胡须似乎有些难以确认,不过也没有完全警觉那悄然潜伏的杀机。
直到死亡不再是零星的噩耗,而是成群结队地叩响家门;直到邻近的几个小县城因疫病而如同鬼域的警示传来,州府大员们才如梦初醒,惊惶失措地拉起警戒。
可惜,一切似乎有些晚了。
当官府的告示终于贴满城垣,当富户们紧闭高门、点燃艾草时,底层的百姓早已成片凋零。
狭窄潮湿的陋巷里,家家户户门口悬挂着刺目的白幡,哭声日夜不绝,又渐渐被更深的死寂取代。
街市空荡,店铺紧闭,只有裹着草席、散发着恶臭的尸体,被麻木的收尸人拖拽着,丢上堆满的板车,运往城外那日益扩大的乱葬岗。
瘟疫的魔爪起初似乎避开了土氏族的高院,只在墙外徘徊,然而,高墙之内并非净土。府中的管事、采买的仆从、洒扫的粗使丫头、看门的壮丁……他们如同维系庞然大物运转的无数微小齿轮,不可避免地要与墙外的疫病世界接触。
当第一个倒下的仆役被发现时,恐慌便如毒藤般在深宅大院内疯长。
纵有高墙深院,锦衣玉食,又如何能抵挡那无孔不入的瘟神?仆役成群病倒、死亡的消息接踵而至,仆役的尸体被草草抬出角门,与巷陌间的贫户尸骸一道,汇入那通往乱葬岗的死亡洪流。
绝望之中,自然也有人萌生了北逃的念头——跨过那条浩荡的大江,或许就能逃离这片瘟神肆虐的土地。
然而,当他们携家带口,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奔到江边时,面对的却是比瘟疫更冰冷的现实:空茫的江面上,连一片帆影都看不见!
这些年,江南士族为了割断朝廷的控制,不惜毁坏连通南北的桥墩,断绝交通。
朝廷岂会坐视?反制之策凌厉而彻底——精通官船营造的匠人,多年来被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太多。
江南空有临江海之地利,却早已失去了建造大型坚固官船的能力,关键的图纸与技艺,早已湮没在阴谋与暗杀的血污之中。
零星的小舟倒是有,可在这隆冬时节,面对浊浪排空、寒风刺骨的浩瀚大江,凭一叶扁舟横渡,无异于痴人说梦。
更令人心胆俱裂的是,也有那不信邪的亡命之徒,侥幸在风浪中挣扎着接近了北岸的轮廓,迎接他们的,却是破空而来的密集箭雨!
北岸的边上士兵的身影如同沉默的礁石,他们的职责就是阻止任何可能携带疫病的“污染”北上。
江风呜咽,卷起岸边绝望者破碎的衣袂。
那些曾为“自保”而力主毁桥、阻绝南北的江南豪强们,此刻是否也在奔涌的江水前,望着对岸模糊的生机,感到了锥心的悔恨?
或许,只有当那冰冷的“刀子”真正扎进自己的肌体,才会在剧痛中悔恨无比。
此次大疫,江南东西两道元气大伤,底层百姓尸骸枕藉,十亭去了四亭;依附于豪族的仆役、佃农、工匠大量死亡,如同被抽走了地基,再宏伟的楼阁也摇摇欲坠。
正如祝长青所深深忧虑的那样,当田亩荒芜无人耕种,当作坊空置无人劳作,当市井萧条百业凋零……这劳动力丧失殆尽的苦果,最终会不分贵贱地,砸在每一个幸存者的头上。
繁荣的江南,在瘟疫与人为隔绝的双重绞杀下,只剩下一片令人窒息的废墟与哀鸣。
二月底三月初,北地,江南大疫已过的消息,终于吹过了冰封的江水,抵达了朝廷和北方的州府官衙。
朝廷的文书盖着鲜红的朱印,字句间却透着未消的戒惧:“江南道疫情初歇,然为防余瘟,官船通行始准。凡南来舟楫,无论官民,抵岸后需锚泊江心,静候十日。十日之内,无一人一畜染疫之兆,方许人员登岸,货物入仓。”
作为被北地控制的官船自然一五一十地实行到底。
二月廿三,长安贡院。
厚重的朱漆大门伴随着沉闷的“吱呀”声缓缓洞开,结束了这场牵动天下士子命运的春闱大比。
人流如同泄洪般涌出,带着疲惫、解脱、狂喜或绝望。
在这片喧嚣的人潮边缘,陈行宁的身影显得有些单薄,他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干裂毫无血色,脚步虚浮踉跄,仿佛一阵稍大的风就能将他吹倒。
连续数日殚精竭虑的笔战,几乎榨干了他的元气,若非左右有秦云飞和秦乐两人如铁钳般牢牢架住他的胳膊,他恐怕早已瘫软在地。
“先生,撑住!这就回客栈!”秦乐的声音带着焦急,努力撑起他下滑的身体。
秦云飞则眉头紧锁,低声说道:“先生,别松劲!马上到了。”
陈行宁勉强点了点头,意识有些模糊,全凭一股意志支撑着,就在即将被搀扶上等候的马车时,他有些混沌的目光遥遥投向了南方——念及那个身影,他干裂的嘴角极其微弱地向上牵动了一下,勾勒出一个温柔的弧度。
那笑容里,有尘埃落定的疲惫,有对远方的无尽思念。
然后身体猛地一沉,整个人彻底软倒下去,陷入了昏睡。
“先生!”秦云飞和秦乐同时惊呼,手忙脚乱地将他抱住,两人不敢耽搁,迅速将他抬上马车,车轮碾过贡院前冰冷的石板路,疾驰向投宿的客栈。
万幸早得卢氏打点,客栈里早已请好了长安城中有名的郎中候着,一番紧张的施针、灌药,陈行宁的脉象才渐渐趋于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