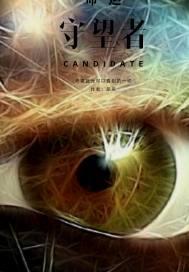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美人欺君 > 第176章(第1页)
第176章(第1页)
烟年忧郁地?问她:“不能直接入洞房吗?”
大宫女瞪她一眼:“礼不可废!”
为巴结叶叙川,护国公府上下颇为卖力,一家老小?齐齐上阵,担起了扮演烟年娘家人的重任,而?叶叙川找来冒充烟年父母的老夫妻则端坐厅中,等着烟年前来拜别。
就?好像天下任何一场婚礼一样,她在众亲的祝福与笑容中出阁,十?里红妆绵延不绝,迎亲的喜乐高昂吉庆,满街张灯结彩,燕雀相贺,在一切喧闹的尽头,她的夫君身?骑青骢马,身?披吉服,迢迢而?来。
自第一眼见他起,烟年就?惊艳于他的好皮囊,他的年岁长些,却正是人生?风华最盛的时候,一张玉面俊美风流,神?采英拔,如高渺东山月,池上青松翠柏一般,教人心驰神?往。
可今日不同,他破天荒地?换了红衣,烈烈如火,矜贵挺拔,好像东山月光坠下人间,沾染了人世间的俗气与温柔。
他含笑遥望着她,目光灼灼,烟年如被?这道目光烫了一下似的,连忙举起小?扇遮住脸颊,
一路吹吹打打行至叶府,见了无数人,说了无数话后,烟年终于走完了全套仪式,由春芬陪着,坐在榻上连连喘气。
她卸下沉重的花冠:“成亲好生?遭罪,下回不成了。”
一旁一个不认得的妇人掩嘴笑道:“妹子说什么话,成婚自是一生?仅一回的大事,何谈再?来一回?”
烟年慢慢悠悠道:“若是我命绝于今夜,那?便真成了一生?只一次的事了。”
妇人笑容僵住。
另几个年轻些的妇人亦停滞住,面面相觑半天,才勉强笑道:“妹子可别吓阿嫂,春宵一刻值千金,今夜可有?许多事要忙呢。”
烟年轻轻“嗯”了一声?。
几名?妇人都是大宅门里浸淫一生?的人,最善于粉饰太平,营造吉祥如意的氛围,她们生?怕开罪叶叙川,围着烟年不断地?说恭维话,可烟年始终皮笑肉不笑,态度冷淡。
前厅喜宴闹了好几个时辰,终于声?响渐熄。
烟年换了家常衣裳,洗去脸上鬼画符一样的妆容,侧坐于床边,等候叶叙川沐浴完归来。
先前撒帐时,床上滚了不少金钱彩果,烟年捡起一枚红枣塞进嘴中,居然一丁点滋味都尝不出来。
她又捡了一枚花生?,用牙嚼碎。
一样毫无滋味。
正此时,鲛绡缬额屏风后传来响动,几个侍女麻利地?收拾了榻上滚落的金银果子,并放下床帘,铺上枕席,彩幔,并细心悬上鎏金雕碧的白檀香球,望之玲珑可爱,风动闻香。
“在看什么?”
身?后响起男人清冽的嗓音,悦耳如淙淙清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