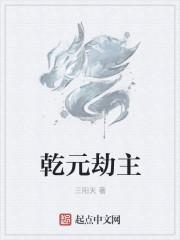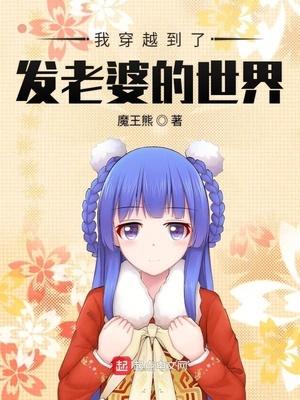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大赢家讲的是什么意思 > 第2章(第1页)
第2章(第1页)
回到酒店我赶紧去查电子书,梁万羽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下了约翰·缪尔的句子。我对这个人物的好奇心一下子被拉高了。
说梁万羽的经历完美地覆盖中国股市的发展显然有些夸大其词。
从华旦大学毕业后,学管理出身的梁万羽进入上海市黄浦区一家银行的全资信托子公司的信贷部工作。那是1990年夏天,梁万羽到岗的时候距离上交所开业不到半年,信托公司证券部柜台每天都排着长队。工作人员在小黑板上写证券行情,飞乐音响、延中实业……有时候价格刚写上去就变了。
股票转让动不动就几千上万,队伍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人急吼吼地抖出腰包里所有现金,“侪部买进,好买多少就买多少!”有人卖掉股票,搓着手哼着小曲儿就离开了。梁万羽连续好几天下班时段都看到一位40岁上下的男子,戴一顶棕色软呢帽,一副棕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在柜台边目不斜视地围观,不时在褐色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梁万羽每天跟钱和有钱人打交道,他打趣自己像个高级酒店的服务生,口袋里紧巴巴的,看到的却都是浮华人生,非富即贵。这个一米七出头的小伙子瘦筋筋的,头发有些自然卷,言谈举止一脸生涩。一个月一百多块的工资,他恨不得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他甚至不舍得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大部分时间还在穿大学时的衣服。可同事们都衣着光鲜,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40岁出头的信贷部主任许志亮,进出总是一身时髦的金利来,兜里还揣着红塔山。
虽然大学在上海待了四年,走出学校,梁万羽还是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他来自四川山区,高中毕业前也没正经说过几次普通话。大学四年下来,他的话越来越少。为了争取学校里屈指可数的留沪指标,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
公司里上海人居多。两个上海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旁边的人听不听得懂,他们总是习惯讲上海话。这种或许并不刻意的行为,很轻易就把人排除在话题外了。好在许志亮也是个普通话不标准的外地人,梁万羽有事没事就跟他请教。梁万羽勤勉,机灵,干什么活儿都一丝不苟,不管端茶倒水,还是免费跑腿。
虽然没什么存在感,但这份“服务生”的工作很快为梁万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到岗没几个月,许志亮带着梁万羽去深圳学习。搞改革搞开放,上海、深圳两个城市一直暗中较劲。
在深圳的最后一天,点完卯,许志亮就带梁万羽溜出会场,找他的老乡许德明吃早茶去。许德明带他们参观当时声名显赫的深圳国贸大厦,一路上介绍自己这几年的变化。
许德明中等个子,身穿藏青色休闲西裤,一件白衬衣规规矩矩扎进裤腰。他是一名工业设计师,以技术人才的身份从河源借调到深圳的南头区,也就是现在的南山区。深圳不仅待遇远超周边城市,机会也非常多。一个技术人才,比如财会、法务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同时做几份工,拿到非常可观的收入。许德明到深圳。
早在1983年,深圳就发了股票。股份制公司的干部拎着公文包到处兜售。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的股票每股10元,但不退本不付息,接受度并不高。人们普遍没什么闲钱不说,就算有点闲钱也更愿意买债券。有传言说,万科发行股票时承销的证券公司最后砸了好几百万股在手里。
许德明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他托朋友从香港买来股票书籍,学习投资理论和技术分析。金田的股票发出来,转让价格很快被推高。许德明决定不再等待。他找到卖家,拟了一份转让协议,签字画押。如果这股票最后需要过户或者再次转让,可以请卖家协助完成。
许德明凑了9000元,买到600股金田的股票。而就在1990年5月,深圳股市涨得摁不住。政府连续出台限制涨停幅度,从10的涨停板限制升级到1,开征印花税,还来个什么入息税——股息红利如果超过一年期利率,超过部分要收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每个月拿到工资,许德明先把生活费交给老婆,剩下的钱就拿去买股票。以许德明太太的收入,根本不需要他补贴家里的开支,但作为一个男人,许德明觉得那是他的责任。在早茶馆,许德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向许志亮展示他每次购买股票的名称、时间、价格。有的股票后面还断断续续地更新着不同时间的价格。
许德明点了一桌吃的,白煮虾、白切鸡、猪油渣炒菜心、小笼包、凤爪、馄饨……许志亮似乎对股票也很熟悉,两个老乡热烈地讨论着广东一些传言会很快上市的公司。梁万羽听得入神,根本顾不上吃。在信托公司柜台瞥见那些股民,梁万羽只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蒙太奇,从没有过代入感。跟许德明坐在同一张饭桌上,这件事情马上变得真实起来。还真没看出来,眼前这个斯斯文文的工业设计师,一出手就魄力十足。他自己都说了,几年前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四五十元。
9000元啊,去哪里弄9000元?政府打压,不让卖了怎么办?亏掉了怎么办?怎么就敢那么大一笔钱砸进去?
“政府这么打压股市,许大哥你怎么还敢买?”梁万羽怯怯地问。
“打压是真的。但政府一再出台政策限制股市上涨,恰恰说明现在大家对股票的热情很高。”许德明抓起筷子,一边给许志亮和梁万羽夹菜一边说,“反正我现在每个月有工资,太太也在挣钱。生活不用担心。但我们要对新生事物有信心。我们大老远跑来深圳,还不就是对深圳有信心吗?深圳特区刚成立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五层楼都是高楼。刚才我们去看的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呢!这就是深圳!别小看我一个月一个月地零敲碎打,我要是把手上的股票都卖掉,我已经可以在深圳买房子了。退回去几年,我哪敢想这些?”
许德明的故事像黑夜里的一盏灯,照亮了梁万羽。
回到上海,从单位宿舍到办公室,梁万羽的思绪长久地沉浸在深圳的早茶店。只是他还拿不出一分钱来买股票。
刚工作这几个月,每次发完工资,梁万羽总是第一时间往邮局跑。能够从川西农村跑出来,在梁万羽看来,一切都是因为他那贫困却充满爱意的家庭。他想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让父母过得更轻松一些。
梁万羽反复琢磨一个问题。深圳市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干部炒股。相对而言,干部队伍显然更了解政策,更了解企业。这些企业的主管、运营,都来自干部队伍。他们敢花真金白银去炒股,一定是得到了某些强化信心的消息。这些人最初也不敢买股票,只因为在其位得谋其政,勉为其难带个头。但短短几年下来,他们的态度已迅速转变。
深圳的股票热梁万羽早有耳闻。7月份上海的报纸就说,深圳的证券公司,从早到晚几百人围着。为数不多的几只股票,都是翻着倍在涨。
上海也不遑多让。证券业务柜台交易开通后,那些率先吃螃蟹的人一直躁动不安。梁万羽上班路上经常碰到有人凑上来:“股票有的伐?”
但这毕竟只是少数有钱人的游戏,勇敢者的游戏。在认识许德明之前,这些东西对梁万羽来说都只是报纸花边、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多人进进出出炒股票倒卖国库券,也只是他人的世界。现在,梁万羽不这么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