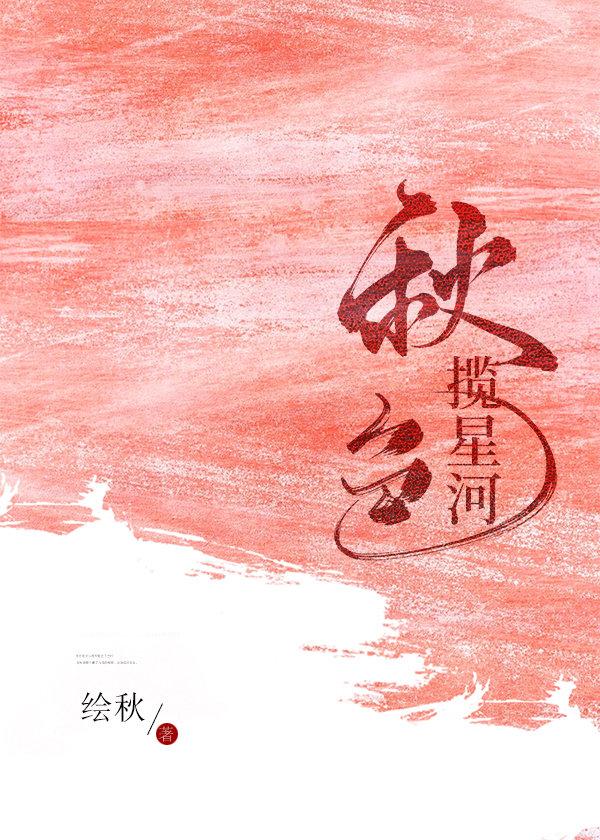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地主家的俏哥儿_林书漫256 > 第 15 章(第1页)
第 15 章(第1页)
沈泊君也皱着眉头,思来想去,便让周管家随他去书房,坐在书桌前,紧急写了一封信,原本已经装好了,可是写上收件人的时候,又迟疑了,将信放进衣袖里,等等再送。
就在这样紧张的氛围里,晚饭都吃得不安生。
县丞府上的气氛却更加紧张,李中举被打之后,李及第勃然大怒,说什么都要把杜家给抄了,人还没有清点好,便听到上头来人了。
对方拿着神武大将军的令牌来,说一批军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丢失,要李及第半个月内找到,不然就要革除他的官职。
李及第哪敢不听,立马调遣人员去搜寻军银。
“大哥,难道你就放任着那个杜舟不管了吗?”李中举气急败坏的问道。
李及第看着还未走的副帅,骂骂咧咧道:“杜舟杜舟,那个泼皮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的事情先放放,我要是官位不保,你也跟着倒霉。”
李中举心有不甘,却又分身乏术,只能偃旗息鼓一段时间。
许汉生被打的惨兮兮,其实打他的是赌坊要债的朱哥,他被杜家赶走的事情很快就被朱哥知道了,便带着人上门堵他,横竖把他打了一顿,他在衙门门口等了好久不见后续当做,反而看到了一批气势十足的人进去之后,便灰溜溜的走了。
这个没钱可怎么办啊?
许汉生眼珠子又转了转,他不能白被杜舟打,一点好处都占不到。
沈泊君坐立难安了一天,让周荣将杜舟和赵奉邺远走的行李都收拾好了,马车就停在后门,若是有人来抓他们,立马就能走。
小虎在外面打探消息,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将自己所见所闻说了一番,李及第带着所有的衙内出去巡山了,不知道在找些什么。
沈泊君稍微安心了一些,等到夜深时,周荣的邻居的三舅的大侄子媳妇的弟弟,带来了消息,他正好是在衙门里当师爷的,说到李及第不会再管李中举的事情。
杜家人才将心放进肚子里,不过却也没有确确实实的安心。
只有赵奉邺事不关己的,一点都不畏惧。
如此过了几日,杜舟在家安安静静的待着,也不敢出门。
这日一大早起来,沈泊君便将宅子里所有人叫到了大堂里,吴叔正战战兢兢的跪在冰冷的地面上,拼命求饶。
沈泊君在立加法,吴叔在杜家干了十几年,竟然伙同外人陷害少东家,还到处传播有辱杜舟名誉的传言。
他本来又在跟宅子里的下人说杜舟的事情,被周管家撞了个正着,他又是痛哭又是发誓,让沈泊君顾念着这么多年的恩情,放过他。
沈泊君原本还想抓他去见官的,想了好久,最后还是将他逐出杜宅,永不再用。
杜舟因为心神不安,都没有睡好,他醒来时候,已经错过了这事儿。
他去跟沈泊君请了安,沈泊君安慰了他几句,道:“事情都过去了,你也别再忧心,有时间出去转转。”
“好的,父君。”杜舟应道。
回去之后,翠儿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绘声绘色的说给杜舟听。
杜舟听到翠儿说的事情之后,他不由惊道:“许汉生被人打?这……这是怎么回事?”
“少东家也别忧心,这事儿与你无关,沈老爷派人去查过了,那个许汉生之前说是在城里找活做,哪里是正经行当,缘是在那种地方声色侍人,还沾染了赌习,在外头欠了好些钱,混不下去了才来乡里躲债的。”翠儿说到这里,心有余悸,“好在少东家你发现的早,不然可就搞了个丧门星回来。”
杜舟听得一愣一愣的,半响之后又问:“他被人打了,与我何干啊?”
“就是债主找上门了,他正好被我们赶出去,就说他有法子还钱,便搞了这一出,还有那个姓吴的净会信口胡说,把许汉生这种人带进府里来,吹得天花乱坠,他欠债被打得半死的事情,十里八乡人尽皆知,还想往我们家扣屎盆子,呸。”翠儿骂骂咧咧。
杜舟拧着眉头,又道:“吴叔怎么处置?”
翠儿不忿道:“赶出去永不再用,真是便宜他了。”
“那许汉生现在在去哪里了?”杜舟拧着眉头,总觉得有些不安。
翠儿想了想,道:“李中举不管这事之后,他便消失不见了,指不定被人给打死了。”
杜舟非但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更加惆怅了,道:“也是可惜了,有手有脚的,为什么要去赌?”
“少东家同情那厮干嘛,想到上次分家时候,家里人手本就少了,这年关将近,你又要成婚,门房告假,吴叔这个内贼被赶走,我们都忙不过来了。”翠儿有些惆怅的说道,现在家里的人恨不得一个掰成两个用,可事情还是处理不过来。
主要就是那个吃闲饭的,什么要腊月二十八成婚,这又要过年又要办理婚事的。
想到这里,翠儿忍不住说道:“那个表少爷,真是个懒汉,身体早就好了,偏偏干吃闲饭不干活,还总是出门,之前他可是打了衙役,要是被人看到抓了去可怎么办?”
“你又在说我坏话?”赵奉邺冷冷的声音从屋外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