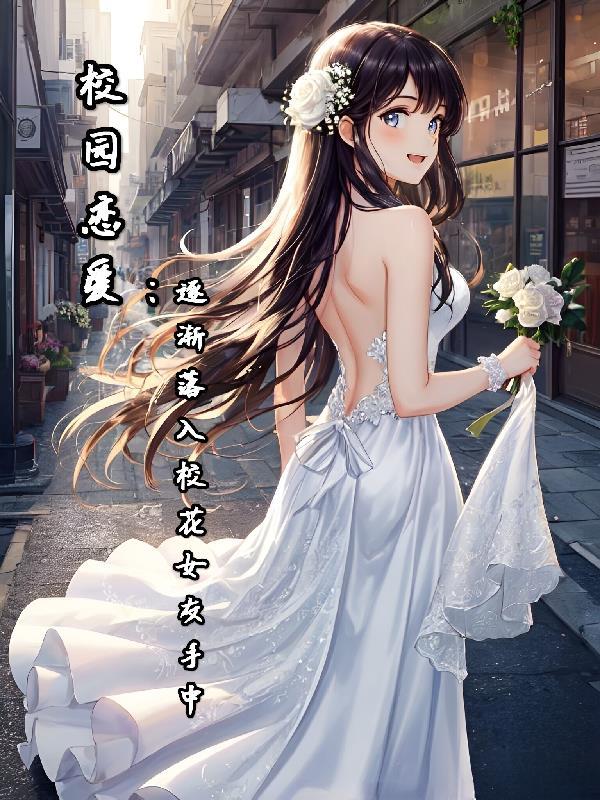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心机美人翻车了 > 120130(第21页)
120130(第21页)
宋怜微怔,要从榻上起来,林霜抿着唇,按着她右肩让她躺下,声音低了两分,“我没有受伤,只是你将我舍下,独自离开,你受了许多伤。”
林霜陡然知道对方离开江淮时,已是五日后了,她有心瞒着行踪,谁又能寻到踪迹,她被遗留原地,没留下一句话,一封信。
她离开庐陵,往北,往东,最后往西,走遍州郡,在蜀中发现女君的踪迹,她知她为何离开庐陵,遇到名山名水时,听见有隐士名士,也壮着胆子去拜访,想帮阿怜请得一些能人贤才,只是世上多沽名钓誉之辈,听她的主君是女子,不嫌她污了名声唾弃咒骂的,也似听见天大笑话一样,鄙薄大笑。
她一家一家拜访,终失望而归,转而提起笔,将路过的州郡绘制成舆图。
白日里寻人,夜里绘图。
现在厚厚的一沓册子正放在她手边的包袱里,林霜抑制不住想拿出来,但知道她很累,便也暂时忍住了,只是道,“我知道你的好意,你要走的路很危险,你不想我跟着冒险,将来丢了性命。”
但阿怜又怎知,她愿意追随她,同她一道赴死,只要是她想做的,不管上天入地,她都会追随。
哪怕下场是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之痛,她亦能承受。
林霜嘴唇动了动,话堵在喉咙口,最后看了眼车帘的位置,“我也可以和来福,和清莲姑娘,清荷姑娘一样,你若是败了,我立刻倒戈,向赢家投诚拜倒,换活命的机会。”
车帘并不隔音,清莲吁了一下马,掀开车帘,往里面瞪了一眼,“奴婢敬佩你武艺比我们强是真,但姑娘您怎么乱造谣,来福小先生待女君一等一的忠心耿耿,我和清荷,不仪仗女君根本活不下去,怎会背叛女君。”
她说着,对上粉衣姑娘坚定的目光,忽而明白过来,她哪里是要给自己找后路呢,只不过是如同她们一样,要女君放心将留下她罢了。
听着话里的意思,是女君旧时的人,千里迢迢寻来这里,一路上又岂会容易。
清莲心软了一分,知她没有恶意,恐怕是个不擅言辞的,便不在意了,看了眼天色,从袖子里衣最里侧的袖袋里取出药瓶,反手递进车帘里,“女君背后有杖伤要上药,阿霜上一下。”
难怪是趴在榻上的。
林霜接了药瓶,抿了抿唇神情黯然。
宋怜大约能猜她想什么,边伸手去解衣裳的绳结,边温声道,“这是必要的步骤,再强的武艺护在我身边也无用,只是看着可怖,并不怎么严重,阿霜勿要挂心。”
轻软的绫罗滑落,本是玉色凝脂的肌肤上伤痕遍布,有些发红,有些已皮开肉绽,左肩处半寸的伤口结了痂还未好全,当
是箭矢贯伤。
林霜别开眼,视线又落回背上,从架子上取下干净的巾帕,沾了烈酒擦拭,见榻上的人埋在床褥里,肩胛骨连动也未动一动,她反而下不去手。
究竟受了多少伤,才能这般忍痛。
清莲每次上药,必是泪眼汪汪的,宋怜生怕林霜也这样,忙抬起头问,“阿霜有阿宴的消息么,他可曾好。”
并不是太好,女君离开以后,夜幕以后她常见平津侯立在楼台之上,看着女君离开的方向,身形萧索,来回踱步,相隔甚远,但那浓厚无法排解的思念,叫她心有戚戚。
但女君既已舍下平津侯而去,平津侯不远追随女君来蜀中,便也不必多说,叫女君平添烦恼了。
林霜只应了声好,偶尔伤寒,并无大碍。
于江淮来说,平津侯无疑是好官,“侯爷勤政,治下有方,江淮百姓安居乐业,非但百姓对他爱戴,连士族学子都十分敬仰他,奴婢走过南北,侯爷的名声威望,几乎要同北疆王平齐了。”
北疆以强盛的兵事俯瞰大周王朝,他收获名声的来源,除却一身的学识品性,还有其在北疆重蓄实力养精蓄锐的这几年里,四处派兵镇压叛乱,替周边各郡县除匪贼兵患,百姓自不必说,许多小诸侯势力,或是已有兵马的将军武将,因敬重高兰玠,自愿领兵投诚的也不在少数。
蜀中起步得晚,走起来处处受掣肘,姑且比不上江淮北疆,她不是真正的贤德之士,周弋没有真才实学,想如同阿宴一样,得道多助,短时间内不可能做到。
也没办法似高兰玠,大国强兵的底气,世家贵子,十二岁进军营驻边关,十三岁小有捷报,十六岁与羯人交战,大捷,声名就此显赫,此后百战百胜,二十二岁偃武修文,因学识品性受世家清流追随倾慕,国公府灭门案以后,自羯人手里夺回恒州,高家军沉冤昭雪,十数万高家军平反。
这样的人想得人追随拥戴,实在不算难。
宋怜半阖着眼,思量吴越几方势力强弱,以缓解背上叫烈酒和伤药激出来的剧痛。
那修长纤细的脖颈上滚落水珠,竟是从发髻里落出的汗珠,沾湿散落肩背的发,林霜便知上药带来的痛楚,并不似她表现出的这般云淡风轻,连她放下药瓶先去净手了也未曾察觉。
林霜抿抿唇做坐了回来。
眼前放来一叠厚厚羊皮,左侧用麻线封着,看得出经常拆装的痕迹,入眼的兽皮被削得很薄,看起来崭新,上头写着图册两字,墨字不算有形,但看得出写得极认真端正。
林霜见过女君的字,常用的字秀丽端方,写在绢帛上叫人看着就赏心悦目,林霜见女君的目光落在字上,脸上重新烧红,僵坐着忍住要夺回重写了来的冲动,“是我绘的图册,沿海兴王府共有六郡,是城街图,海国三郡,徐州两郡,郑州三郡,除了城街图,还有一点山势地埋,不知你用不用得上。”
先前在江淮,跟在她身边,偶尔听她同臣僚议论政务,和江淮丞相也议论兵事,她记下女君说的,兵战起时,非但城防重要,一些山脉峡谷,关隘江河也很关键。
她也不知道该打听哪处山脉山势,到地多听说书人讲郡县里过去的历史,尤其是打过仗的战役,总想着将来要是有用,能帮到她就好了。
宋怜只听她走过这么些地方,已十分震惊了,知她恐怕是为了寻自己,看着她失神,好一会儿后才去翻羊皮卷。
绘制舆图是件难事,县衙、甚至是州郡里的工曹匠作,也未必能做得来,未学过天象数术,单就辨别城郭座记、各街各坊方位都难,度量尺寸、绘图,哪一桩都不容易。
林霜并未学过,宋怜翻开时只担心她受了翻山越岭的苦,最后却做了无用的事,已是决定无论里头写的什么,画的什么,都说是有用的,她对勘看舆图、测绘感兴趣,她以后教她便是了,纵是一时忙不急,先请了先生教她绘画数术,学了绘画数术,她恰好知道大周谁擅星象,再请来教她学一学星象也未尝不可。
知道女孩正一瞬不瞬注意着她的神情,宋怜神情维持着肃正,翻开第一张,复杂却有条理的舆图映入眼帘,宋怜呆住,“这是阿霜绘制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