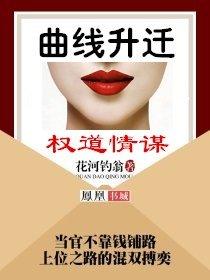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神君他又想渣本座[重生] > 第276章(第1页)
第276章(第1页)
“三长老在这座城里不见天日了一百三十八年,是不是早已忘了,他的劫,他的难都是因你而起的。”
晏顷迟不动声色的看着他。
“晏顷迟我其实真的很佩服你,”沈闲笑道,“你死了一百多年,却还能在坞城声名赫奕,沽名钓誉的笼络人心。”
晏顷迟手上青筋暴起,似是在极力抑制着自己呼之欲出的情绪。
沈闲从他的眼神里窥视到了遮掩不住的阴鸷:“忘了,三长老的能耐也不止是在此处的。”
“强人所难,颠倒是非也是你晏顷迟的所长,”沈闲仿若未觉,接着说道,“你曾经三番五次的想要置我于死地,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我还可以告诉你,自打你葬身在那场劫难里以后,宣城已易其主,你恪守的天道,早已被人践踏殆尽——你看,你同萧衍的理念当初就是背道而驰的,哪怕现在也是南辕北撤。”
这样不作遮掩的讥讽和恶意,让屏风后的萧忆笙都怔住了,他听着沈闲言辞里的阴冷,微微变色。
沈闲想看到晏顷迟的失意,失望和渴慕不得的怅惘,他想窥探到来自晏顷迟的失落。
然而晏顷迟只是敛下眼眸,沉默着,并不作答。
“呵。”沈闲见他缄口未言,忽然笑了,笑里意味难明,有着报复的快感,“罢了,其实你现在不过是个死人——”
话音未落,眼前倏地有黑影拂过,沈闲猝不及防,呼啸风声已至耳边。
“啪”地一声清脆的重响,突如其来的力道扇在脸上。
火辣辣的痛感的登时蔓延开,沈闲的话被打断,他死死盯住晏顷迟,抬手覆住被扇的地方,忽地讥诮两声,没有再说话。
“沈闲。”晏顷迟沉声念道。
“你没有任何资格指责我。”他淡淡地说,“也请二阁主知道,这世间上很多事情不是空凭着舌绽莲花就能解决的。”
“你说得对,我不喜欢你,是因为私心。不过于公,我依旧不喜欢你,”晏顷迟眼风上下一掠,以一种极其冷漠的目光打量他,“你应该知道自己孤身前来,只要我想,你就再也踏不出这道生门了。怎么,又想用萧衍来挟制我么?”
他收回视线,不再看沈闲:“一个七尺男儿,还需要靠所谓的妻子来庇护,连镳并轸都做不到,只会坐而论道。你与其冠冕堂皇的指责我,不如先学会如何孑然立身,否则你这辈子也只能活在别人的余荫下了。”
晏顷迟说罢,轻拍自己的手,似是在掸去瞧不见的灰尘:“这巴掌是我今日要教给你的道理,希望二阁主以后也能师夷长技。”
“不必言谢。”他微笑有礼。
沈闲一字未言,只是抬眼看着他,目光停滞在他身上,透着冷意。
“等等!”再也忍不住,萧忆笙陡然出声,“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