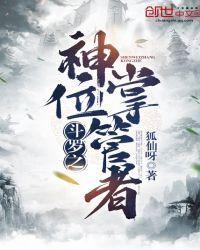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女商(大清药丸) > 第203章 第 203 章(第3页)
第203章 第 203 章(第3页)
有一日林玉婵照常上工,发现周姨捧着一张宣传单,正央求常保罗给她读。
“……是以前做丫环的姐妹给我的。小常啊,我这半辈子辛苦,攒下一百两银子不容易。你帮我看看,这地皮股票靠谱不靠谱……”
英联房产公司的初始五十两银子面值的股票,此时价格飙升到将近八百两。但是没人肯卖,都捂在手里,都觉得股价会再创新高。由于严重供小于求,股票价格一天比一天高。
但,有那心细的郊区居民已经发现了。太平军战乱结束后,上海市郊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迎来难民压境。大量官军驻守城郊,除了偶尔剿一下叛匪余孽,县城内外平静得好似无事发生。
也没有突如其来的买房需求。相反,租界内外不少房屋都贴上了待售的标志。牛车马车骡车独轮车,载着大量行李辎重,载着浩浩荡荡的男女老少,开始成群结队地离开上海。
自从“逆匪清剿”的消息传来,博雅公司的生意日趋清淡。因为不少供货商和客户,也都回乡了……
苏敏官嗤笑:“马后炮。敢想不敢做。”
林玉婵抢过去,直接把宣传单撕了。低头看看碎片上的文字,并非“英联”,而是一个不认识的房产公司。
“想都不要想。万一他们卷款跑路,你半辈子积蓄没了!”
同时想,这些资本家简直没良心,都坑到不识字的底层妇女身上了!
周姨当然不服,小声抗辩:“那个苏老板说他们会跑路,他们就真会跑路?太太你也不能事事听他的吧!——退一万步,我现在不是丫环,是您的雇工,我的钱财自己做主……”
“你敢买那股票我就开了你。”林玉婵毫不退让,“你看着办。”
“四百两有人买吗?前天还是四百两!——没有?三百五十两?……三百两?”
这边卖盘积压,那边无人接盘,银行里的华人柜员清闲得很,甚至打起了牌。
股民们只能自力更生,有人灵机一动,向过往行人兜售股票:“如今我等急需用钱,这才贱价抛售。大家快来抄底呀!票价马上会回升的!”
还真吸引到了几个不明真相的闲人。打听到地产公司的股票原本面值四百两,如今下跌到三百两,当真是抄底买入之良机,遂跃跃欲试,左右打听。
有人稍微清醒一点,想起来:“那么多新工地,可怎么都停工了呢?大家都回乡,房子谁住?地产公司怎么赚钱?”
“但还款日还没到是吗?”林玉婵立刻接话,“王全抵押时的地价估值虚高,如今地价下跌,据我所知,钱庄有权利立刻催还一部分款项,或是让他补充抵押物。而他手中的股票价值已不足以补充地价的损失,其余的抵押物更没有。所以……您不妨开个价,如果债权人逾期,我可以立刻接手,帮你们免掉时间上的损耗。反正经营茶行你们也没经验,收不到太多孳息,白拿着还要花钱维护——这样,能给多少折扣?”
华掌柜一愣神,不免转头看苏敏官。
这小姑娘什么来头?还满口“估值”、“债权人”、“逾期”、“孳息”,好像她真懂似的!
这是孙武子教女兵,来他这里刷经验来了?
苏敏官专心鉴赏会客室内的一套棋具,漫不经心说:“跟她谈啦,我不管的。”
华掌柜当然不会信,满心想:这小少爷玩票玩得够广泛,上次买轮船,现在改制茶。明天会不会去关外挖虫草?
林玉婵:“哦对了,清退和过户的事,自然是钱庄代劳的对吧?毕竟你们更有经验。如果您拍板,我可以先付定金。”
华掌柜壮着胆,悄悄打量这姑娘的五官面容。
湘军淮军步步紧逼,战局如同倾泻而下的山洪,滔滔奔流往既定的方向。
猎奇而血腥的细节传遍街头巷尾。进出衙门的公人脚步轻快,个个喜气洋洋,都知升官发财近在眼前。
《北华捷报》刊载工部局董事会告租界外侨书,一边谴责清政府对叛军的野蛮屠杀,一边提醒大家做好难民大批涌入的准备。
上海租界的繁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靠邻近省市的同行衬托。外界战乱越惨,租界里的和平越显得弥足珍贵,宜居性遥遥领先。同时,难民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源源不断的住房需求。
林玉婵的预言成真。短短一个月内,地价果然又升一成。投机成性的洋人们成立更多的地产公司,继续筹钱建房,期待能收取天价的租金押金。这些众筹的款子,从洋行银行,到钱庄、票号、私贷,一路剥洋葱似的,摊到广大华人百姓头上。
众人一下转了一百八十度,上百只眼睛看向了那个花白辫子的人——
“老黄!”有人大喊,“你不也是苦主?你怎么走了?你不要银子了?”
一下子十几人叫起来:“黄老板,你怎么走了!”
有人认为城内百姓已与叛匪同流合污,死有余辜;有人暗暗叹息,不敢多言;唯有那一众洋人地产商,捧着报纸眉开眼笑,心中盘算着等难民涌入,自己的地皮生意又能扩张多少倍。绕路拐上外滩,还没喘口气,又看到几家英资银行门口排出长龙,无数穿长衫的体面商人如坐针毡,在闷热的天气里排大队,衣衫汗迹斑斑。手里捏的,包里揣的,全是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