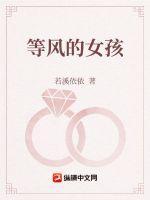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替身悔婚之后 > 第327章(第2页)
第327章(第2页)
加之他母妃去世,他又重伤不醒,诸般不顺层叠而上,重压在先皇的肩头心上。
只再加一尾轻飘飘的鸿羽,便能轻易压垮他。
更何况……
他那时方醒,格外虚弱,只当时先皇以为他难以清醒,为了稳定国本超纲,便立了赵修翊为太子。
又怎知个中曲折。
垂首,赵修衍看向怀中人,“瑟瑟,生于天家,当以江山社稷为重。”
即便他有心暗示,先皇或也会只作充耳不闻。
比起储君未立,轻易改换储君更容易动摇朝纲,催得一些人汲汲营营。
再者……
“瑟瑟,你应当知道,沈太后做下的事不止这一桩。”
仅是他重伤,或只会让先皇动摇,远不止即可定下储君人选。
除他之外,四皇子、五皇子也已初立功勋,在朝中稍有立足之地。
阮瑟蓦然垂眸,不愿再与他对望。
好半晌后,她才迟迟开口,“所以,这才是你偏帮谢家、为兄长平冤的初衷,对吗?”
是为她,也是与谢家的交易。
更是不愿她长兄再如珠蒙尘,是对他自己的昭彰慰藉。
话落,阮瑟立时便感觉到揽在自己腰间的力道又收紧几分。
上方亦传来男人略显无奈的应声,“是也不是。”
“楚家移花接木,偷换得谢家人的军功,此事在我之前。”他的嗓音依旧低缓如沉,一点一滴地道尽过往,“后来隐隐有败露的迹象,楚家便向沈太后投诚,又故技重施。”
只不过,被筹谋的人换成他,换成惠妃。
“皇兄与我同在边关抵御西陈,文韬武略皆不输我。或是天意弄人,他晚我两年才大破西陈,得以封王。”
即便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阮瑟早已从高瑞口中得尽因由,可此时再听赵修衍亲口提及,她心里还是浮现出一种难言的滋味。
下意识拽紧赵修衍的衣袖,她接道:“所以沈太后就与楚家……”
“趁你昏迷重伤时,又改换军功,是吗?”
沂州、彬城之战,原该是他大建功名之时。
而今被边关铭记的,只有金銮殿上的人。
青史亦然。
沉积谢家多年的怨苦可得昭彰,他却不能。
一步咫尺,一生遥遥。
悯然与惋惜愈发蔓延,裹挟着不可名状的心疼,缓慢而坚决地卷席上阮瑟心头,教她再难启唇相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