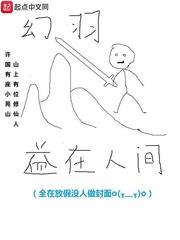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快穿之驯服虐文男主 > 第 474 章(第1页)
第 474 章(第1页)
。
魏恬松了手,抱着自己的左手,浑身上下湿得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前襟和脸上都沾了不少血,可饶是如此,他也一声不吭。
脊柱颤抖着,身体蜷缩在地面上起伏不停,直到过了很久,沙哑的嗓音才从手臂间挤出。
“阿辛伤了脸,魏恬赔一只左手,陛下可满意?”
沉默而极具的痛苦有如实质,挤满了书房,堵在所有人的心口,沉甸甸的。
朱珠知道魏恬有多重视他的手。
右手手筋被原身挑断后,他一度颓废偏执,是靠着“左手习武”的信念才撑到了今天。
而这一砸,相当于把他整个人的傲骨给砸碎了,将自己的残疾血淋淋地扒开摊着,暴露在阳光下。
他的左手手背上几乎没有一块好ròu,断裂的骨茬刺破皮ròu翻卷出来,哪怕经过治疗,也会扭曲变形,终身都无法复原。
曾经骄傲自满的魏小将军毁了双手,就如同斩断了鸟雀的双翅,将他变作匍匐的虫豸。
朱珠只觉得,这个栽赃嫁祸虽然愚蠢,却实在好用。
人证已死,物证俱全,魏恬偏偏还不是她心尖尖上的男人,一旦被泼上脏水,必然百口莫辩。
哪怕他断手自保,朱珠在日后看到阿辛脸上的伤时也会反复想起,魏恬和顾青岩,害得她的“宝贝”毁了容。
这条攻心的毒计,很像某人的风格。
若她是原身,恐怕不会让顾青岩和魏恬受这个委屈,只可惜她是任务者,为了激化矛盾,她只能捂住眼睛、蒙住耳朵,让这场戏愈演愈烈。
——现在她要做的,就是抛却多余的同情,钓鱼执法。
朱珠清了清嗓子:“此事就此揭过,明月,送魏公子去诊治。”
魏恬离开后,染血的地砖很快被擦拭一新,空气中也换上了新的香炉,将血腥气驱散一空。
付卿卿不声不响地继续给她按摩额头,朱珠靠在椅子上,突然感到有些累。
就像是飞久了的鸟,哪怕沿途再精彩异常,也总会感到疲倦,想停下来歇一歇。
大脑难得有些滞空,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想贪图这片刻的宁静。
一把银簪的尖端,无声无息地抵在了她的颈动脉。
付卿卿的身上完全没有杀意,他如同无害的绿植,当他想刻意降低存在感时,朱珠真的很难不忽略他。
身上陡然被激出了一层冷汗,耳畔是他雌雄莫辨,温和而缓慢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