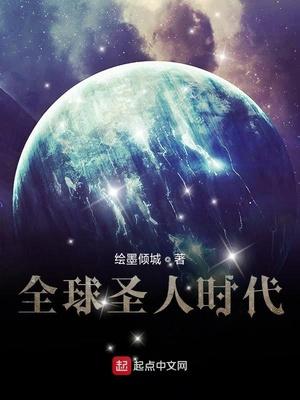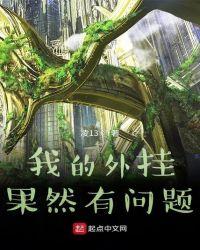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凤谋金台 > 160167(第2页)
160167(第2页)
“你心疼边疆的百姓,心疼受苦,那你也能不能心疼心疼我,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此
徐圭言看着他,听着他剖心掏肺的话,没有流泪,却有一种更深的情绪从眼神里溢出来——一种源自对权力与感情深渊的彻底冷静。
“你想知子之争?不是为了谁登基,也不是为了什么名声。”
“冯知节那日跪在太极殿外,我偷人,李林,被关在地牢的样子,也是那他说话,没人在意他曾护国之功,只想求一个解释,可没有人给我。”
“这天下,对错从来不是靠道理撑起来的,是靠人——有人站出来,说‘这不对’,这事才有了变化。”
“我明白,这一仗我可能赢不了,我知道我可能会死,也知道我一开口,可能牵连你,
“可我不能再什么都不做。”
她望着秦斯礼,缓缓道:“我在朝堂上见惯了用沉默换安稳的人,朝堂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揽财夺利的舞台。我若也变成他们,那我这十年读书、进仕、算计、挣扎,为的又是什么?”
秦斯礼慢慢跪坐下去,像是撑不住身上的重量。他双手撑着地面,仰头看着她。
“你变了,徐圭言。”
她淡淡地说:“是,我变了。因为这世道逼我变。”
徐圭言知道,她这一路有过许多动摇,可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有一种东西始终不能变,那是她为之奋斗的理由。
幸运的是,这一路,经历这么多,她这一点从未变过,反而越发得坚定。也在许多念头动摇的时刻,许多因为懦弱而想退后,臣服于人性裂缝之间的时刻,她做了没让自己午夜梦回失望的事。
曲曲折折,好不容易认清了本心。
窗外风吹动竹影,正厅内静得只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秦斯礼低声说:“你说你若输了,要我不为你哀悼。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赢了,却回不来了呢?”
这句话不是控诉,也不是挽留,是一种源自本能的惧怕。他不是在威胁她,而是在告别一种可能——那个他们曾在凉州春夜、灯下对坐、彼此托付未来的可能。
徐圭言看着他,眼里闪过一点点动摇,片刻后,她缓缓蹲下身,握住他的手——他手很冷,指尖像霜打的枯枝。
“我不想回不来的事,有人必须走这一条不能回来的路。秦斯礼,你很好,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了,好吗?”
她说完站起身,重新收拾衣襟,走到门口。
门被推开,日光照进来,徐圭言的背影融在光中,无所畏惧,极度孤独。
秦斯礼坐在地上,仰望着那道背影,一滴眼泪滑落。
冰凉的泪从他的眼中接连不断地掉下来。
冯知节被贬的消息在长安城彻底坐实那天,天刚下过一场小雨。
秋日来临,一场秋雨一场凉。
街道边的石砖泛着青光,凉意渗进骨头,长街上张贴的告示在风中猎猎作响。
冯家的门前已冷清许久,往日来往求见的人不再出现,仆从也大多散去。府内旧事终了,冯家的传说也在一夜之间变得缄默无声,
城中茶肆里再也听不到“冯将军如何一战破敌”、“冯竹晋如何气压百官”的评书段子。风吹过冯府旧墙,灰尘浮动,连门前乞儿都开始绕路而行。冯家的名号,从金戈铁马的荣光,变成宫中谁都不愿提起的禁忌。
市井传言说,冯将军虽贬去江南,却也保全一命。
可是谁都知道,兵权被夺,远调江南道的某个“江防副都督”——那不过是个挂虚衔、无实权的闲职。
冯知节一去,不再掌兵,边疆的吐蕃也开始蠢蠢欲动。
这件事传入宫中后,许多老臣闭口不言,年轻臣子更是不敢有异议。朝局未定,谁也不敢冒头。而这时,李起年第三次上表求见圣上——依旧石沉大海。
日头偏西,午后宫门仍紧闭着。
而就在这天下午,乾清宫门前,一辆灰色纹缎的宫车悄然停下。
李文韬身着紫袍,被一名太监亲自引入正殿。他原以为是陛下召见自己,未曾想到,一进殿门,映入眼帘的,是着了朝服的长公主李慧瑾,端坐在侧。
她今日不同往常。
平日里她衣衫素净、神色温柔,而今却着正装、凤钗垂耳,面容肃穆,目光直视前方,宛如昔日后唐掌权的太后,不容轻视。
李鸾徽今日亦不在寝宫,而坐在正殿首座,披着金线龙纹的织袍,双目略带倦色,却有一种久违的清明与坚决。
李文韬一进来,先是一怔,随即缓步行礼。他看到长公主面无表情地扫了自己一眼,没有多余寒暄。他下意识地意识到,今日之议,非比寻常。
李鸾徽语气平缓,却不容置喙:“朕和慧瑾刚刚商议了一事——这储君之位,不能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