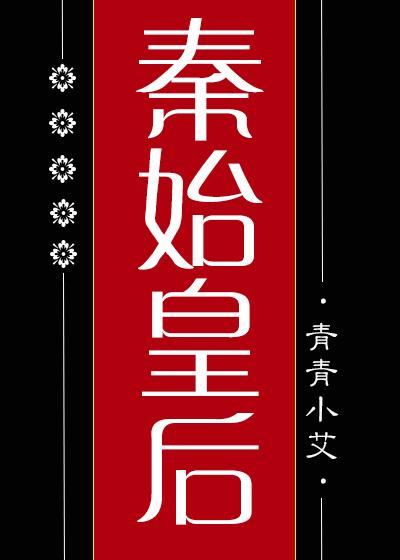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心劫 > 第130章(第1页)
第130章(第1页)
刚才……就在角落里,她失控地占有她,发泄着无处安放的愤怒,而萧宁在最初的抗拒后,最终选择了包容,甚至笨拙地回应,试图抚平她的戾气……
还有……还有她肩头那被细心涂抹的药膏,地上被打碎的药碗,以及萧宁肩头那片深紫发黑、狰狞刺目的指痕……都是她失控时留下的。
每一次危难,每一次崩溃,每一次她以为自己坠入深渊,想要把身边人推开保护时,萧宁都在那里,不是被她护在羽翼下瑟瑟发抖的雏鸟,而是与她并肩站在悬崖边,死死拉住她,甚至试图将她拽回来的磐石。
她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另一种更残忍、更懦弱的伤害,把自己承受的痛苦和绝望,变本加厉地施加在了这个唯一、真正、毫无保留爱着她的人身上。
她成了什么?
和那些伤害她的人有什么区别?用暴力和疏离去对待自己的爱人?
何其可笑,何其可悲,何其……荒唐。
沈今生紧绷的身体一寸寸软下来,卸去了所有挣扎的力气。
她低着头,神情悲怆。
“对不起……”
极低、极哑的三个字。
是为刚才那些伤人的话,为那些失控的暴戾,为长久以来试图将萧宁推开的懦弱。
萧宁又一次地把沈今生重新带了回来,可即便如此,从掌下感受到的沈今生……
仿佛随时会消失般,岌岌可危。
紧了紧手臂,将怀中人抱得更紧,她低声说:“今生啊……现在到此为止吧,别再痛苦了。”
作者有话说:
写这一章的时候我更心疼萧,小沈这个人其实是不健康的,她在逼自己的同时,也在逼着萧。
如果用萧的视角开始这个故事,那么她,是被小沈硬生生拉下了神坛
城楼上的风凛冽如刀,刮过沈今生单薄的青衫,也卷动着远处神策军玄黑大旗猎猎作响,她苍白的手指搭在冰冷粗糙的垛口,目光越过李勣森严的营盘,投向西北方那条蜿蜒的官道尽头。
粮草车队尚未出现。
陈拓焦躁地踱步,靴底踩在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回响,疤狼带人出城已近三日,杳无音信,城内粮缸眼见着就要见底,饥饿像无形的瘟疫在街巷间蔓延,连维持秩序的赤焰老兵眼神都开始发飘。
周通裹紧披风,立在稍远处,望着城外连绵的营寨,脸色比这阴沉的天色好不了多少。
“沈兄弟,那娘们靠不靠谱?”陈拓终于忍不住,“三天了!疤狼没消息,粮车也没影!再这么下去……”
“再等等。”沈今生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一直因伤势而微蹙的眉头豁然舒展,没有半分病弱之气,反倒透着一股沉凝的底气。
连她自己都感到一丝异样。
自那日从十里亭归来,左肩处那贯穿撕裂的剧痛,竟如潮水般迅速退去。
起初以为是心绪激荡下的麻木,可一夜过后,那几乎要将人撕裂的痛楚竟真的大幅减轻。
换药时,老吴头惊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枯瘦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揭开层层染血的绷带,浑浊的老眼死死盯着伤口。
“邪门……真是邪门!”老吴头喃喃自语,声音发颤,“参赞,你这伤……这肉……它怎么长的?”
原本翻卷、深可见骨、边缘还带着秽毒侵蚀后青黑之色的创口,此刻竟已收拢大半,狰狞的裂口边缘生出嫩红的新肉,像无数细小的触手,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顽强地向中心合拢。
深层的血肉虽未完全弥合,但那可怕的炎症和秽毒留下的死灰色泽,竟真如被无形的力量净化驱散,只留下略显粉嫩的愈合痕迹。
这愈合的速度,远超任何参芝续命丸或金疮药所能解释的范畴。
“将军!参赞!来了!粮车!是粮车!”城楼瞭望哨兵嘶哑变调的吼声如同惊雷炸响,撕裂了城头压抑的沉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西北官道。
烟尘滚滚。
一支规模远超预期的庞大车队,正沿着官道隆隆驶来。
打头的,是数百名盔明甲亮、杀气腾腾的神策军精骑,他们队列森严,刀枪如林,玄黑色的甲胄在阴沉的天光下泛着冷硬的幽光,马蹄踏地的闷响汇成一片低沉的雷声,撼动着大地。
在骑兵的严密护卫下,是望不到头的辎重大车,沉重的车轮深深碾入泥土,拉车的健马喷吐着白气。
车上满载的,是鼓鼓囊囊的麻袋,堆叠如小山,那熟悉的、象征着生存希望的粮食轮廓,让城头上每一个饿得眼冒绿光、喉咙发干的士兵和百姓,都屏住了呼吸。
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