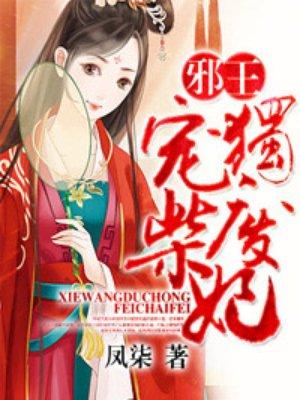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囚她不得gl > 第15章(第2页)
第15章(第2页)
霍祥的话从大脑上光溜溜滑过,我伏在桌上算什么时候溜走比较合适。
下课后,她叫我去办公室。
泡了杯花茶给我,我不接,靠在门上,想变成稀泥从门缝里滑走。
“平时很少见你啊,怎么不来上课。”她语气很温柔,办公室里摆着熏香,不自觉地让人放下心防来。
“这学校的人不都这样?有几个爱上课的。”我抱着胳膊说。
她笑笑:“逃课去公园晒太阳的可不多,你挺特别。”
像烂俗小说的开头,不耐烦地摆手:“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
“当我的心理委员吧,原来那个跟当班长冲突了,不干了。”霍祥说。
是柳愈。
转头看她:“我也不干。”
最后名字还是被报了上去,因着程双言的缘故,我最近上学很勤快。
她开始忙了,又开始每天打不完的电话,喝不完的酒局,常深更半夜醉醺醺回家。
喝醉了,就伏在我身上一遍遍表白,哭泣。
软得一塌糊涂。
也学会了烧醒酒汤,扶着她喝,程双言醉了就耍赖,要我用嘴渡她喝。
我不愿,她就一遍遍亲我,缠在身上磨我,十足赖皮,也十足可爱。
若她总是这样就好了。
次日醒酒后,程双言便回到阴戾的状态里,不怎么笑,绷得紧。
兴许工作压力太大,她近日都没问过我柳愈的事。
柳愈自从上次从我家离开后,便不再理我,路上遇见了,两个人都假装素不相识。
反而与霍祥走得近了。
霍祥年纪不大,是s大毕业的心理学硕士,来我们学校做心理老师着实委屈她。
她时常邀我去她办公室闲谈,或去公园晒太阳。
聊天多了,不免透露些家庭情况出去。
没提程双言与我的事,只说与姐姐同住,也提到父亲去世,母亲已有家室。
她未对我的个人情况发表见解,只旁敲侧击地提到些心理学理论。
整个人被她看透了,并不反感,随着她的手,去逐步探寻自我。
内心的痛苦被剖丝剥茧地理顺,意外怎会有人如此懂我。
“小一,我最近有项田野调查,你愿意配合我吗?”霍祥坐下来,递给我一杯花茶。
“我做的一项课题,需要一个受试者,综合各方面来看,我觉得你很不错。”
霍祥温和地笑,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资料给我。
很长的一个题目,看不懂,只提炼出性取向,心理健康几个扎眼的词。
放下纸看着霍祥。
“我不干,我不是同性恋,你搞错了。”
“上面没说同性恋呀。”霍祥端着茶眨眨眼。
脸有些红,站起来就要走。
“不过我是同性恋,还结婚了。”霍祥冲我伸手,手上的戒指闪闪发光。
“与我爱人在丹麦结的婚。”
![流放后嫁给失忆将军[重生]](/img/15325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