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历史同人] 地府皇帝改造指南 > 第213章(第2页)
第213章(第2页)
不过,同样因为某种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每次带着姓王的刘先生上门为太子辅导,都可以算是穆祺的重大磨难——喔,这倒不是说刘先生每次随同上门都要唧唧歪歪注目凝望爱在心头难开什么的,他还没有这么戏剧化——真正麻烦的是,刘先生拒绝在太子面前行礼。
当然,因为考虑到师道尊严(或者说也有那么一点微妙的感同身受),皇帝是允许了太子的老师们不必在驾前行礼的;但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鉴于老刘家在小心眼记仇上的光辉往事,基本没有几个官员敢在太子面前拿这个大,最次也要行个半礼——但刘先生就不同了,他每次都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略无愧怍的大步走在前面,而两边往往就是低头拱手,预备向太子致意的官吏;于是显得大家不像是给太子行礼,倒像是给他在行礼了!
你几个意思?
这样的特立独行,傲慢无礼,难免会激起意料之中的愤怒;几个常常陪在太子身边的舍人就时而怒目而视,要无声的斥退这些胆大包天的狂徒;但刘先生本人却觉不以为意(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有留意过这些小虾米),于是只留穆祺一个独顶压力,总是非常难堪。
这样的难堪是很难消除的,因为他一没有办法劝刘先生对亲儿子行礼,第二也没有办法让太子左右的侍臣保持冷静,所以只有咬牙忍耐,同时设法在太子面前巧妙转圜,最好别搞出什么大事来。
但很可惜,他的话术似乎还没有修炼到最高的境界,至少太子默默看了他许久,并没有立刻露出什么被说服后恍然大悟,或者慨然心许的表情,他只是道:
“先生仿佛有些吞吞吐吐。”
穆祺:“什么?”
“先生仿佛有些吞吞吐吐。”太子重复了一遍:“是有什么话不方便在我面前谈到吗?”
穆祺:…………
穆祺沉默片刻,忽然道:
“都说殿下肖似今上,以我看来,太子倒是很有孝文皇帝的风范。”
虽然在教学中沉默寡言,常以温柔敦厚的面目示人;但太子冷眼旁观,显然又有寻常人意料不到的毒辣眼光——比如说,他默默围观了很久,就从方士们搞出的尴尬闹剧中窥探出了更深刻、更微妙、更难以示人的东西;而更难得的是,在意识到这种微妙的东西之后,太子居然没有直接叫嚷,找人商量,而是不动声色地忍耐了下去,直到现在才骤然发问,一举掌握了主动权。这样善于隐忍,所谓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心性,确实更像他曾爷爷。
面对方士的夸赞,太子并无喜色。他只是道:
“穆先生先前欲言又止,是想议论那位王先生的事情吗?”
连这都看出来了!
穆祺心情复杂,不觉略微叹了口气:
“殿下说得没错。”
知觉居然这样敏锐,真是俨然有当年孝文帝的风范;所以说大汉朝将来的臣子们真是有福气极了,搞不好费力八劲伺候走一个武皇帝,又要迎来一个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新皇帝,这一辈子的盼头都算是有了。
太子稍一踌躇,终于开口,主动发问:
“……那位王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穆祺叹了第二口气:“连太子也疑惑了么?”
说实话他并不感到诧异。以老登这样大摇大摆在太子书吏面前浑无忌惮的作风,是个有常识的人都会察觉出不对。比如他就非常清楚,近日以来那些书吏的心态已经改变了数次,先是愤怒后是迷惑,现在已经在私下里窃窃私语,议论这位横天横地的方士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到现在为止,天子还没有堕落到让五利将军娶亲女儿的那种疯批境界,所以人们暂时还无法想象一个方士会享受怎么样过分的荣宠;因此,他们普遍只会以为,这位举止特异的“王先生”之所以敢如此大胆,肯定是他的身份非常特殊,特殊到没有敢招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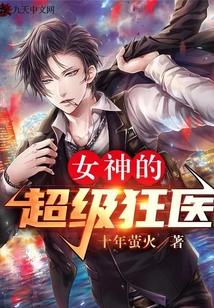

![[红楼]林如海贾敏重生了!](/img/3124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