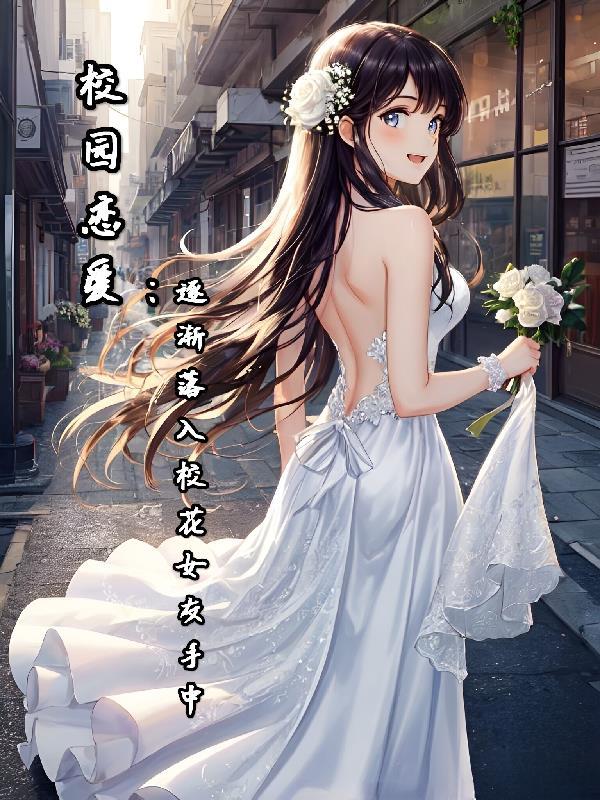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天然呆穿书成恶毒男配后 > 第39章(第1页)
第39章(第1页)
跟着男孩回了家,阿与把渔网往地上一扔,冲进屋里把他妈咪拉出来,手舞足蹈地说,他们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又是扒开裤子给她看伤口,又是声情并茂描述当时有多险,中年女人面色很和善,听完阿与的话,看他们的眼里都有了泪光。
几番交流之后,苏涸已经改口叫女人郑婶。
郑婶一听二人要借宿,就赶紧忙活起来,期间不免要多嘴问上几句。
苏涸知道盛矜与的一切都要保密,就陪着打哈哈敷衍过去。
她认得出盛矜与手腕上昂贵的腕表,也看得出二人身上的衣服虽已湿透略有狼狈,却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恐怕是有难言之隐暂时落难。
郑婶便不再过问。
这个小院算是镇子里经济水平比较好的人家,院里乱糟糟的,一副被风席卷过后的模样,好在屋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腾出一间空房子后,郑婶拿了干衣服给二人换上,又从柜子里抱出两床被子,苏涸被明晃晃的大红色晃了眼,才发现那被子上写着大大的红双喜。
很显然,这是一双喜被。
盛矜与皱着眉头,脸色看不出喜怒,苏涸看他一眼,犹豫着说道:“我们用这个不太合适吧。”
而且那喜被很新,显然是做好了就没拆开过,为喜事准备的东西,让他们先睡了算怎么回事。
郑婶笑了笑,解释道:“这房子原来是我大儿子在住,被子也是给他准备来结婚的,但他走了以后,就闲置了,别的被褥都压在箱子里,又潮又旧不好睡的。”
苏涸以为这个“走了”是去世了的意思,默契地没有再提这伤心事。
他拦住要去收拾床铺的郑婶,把这活揽下来,借助别人家还让主人家干活,苏涸于心不安,而且盛矜与规矩多得很,他要亲自来才放心。
小镇的夜漆黑静谧,只剩虫鸣浪滚的白噪音依稀响起。
盛矜与洗漱回来,推开陈旧的铁门发出扎嘎一声响,就见床边的长沙发上铺着一床被子和枕头,而苏涸正跪在床上撅着屁股换床单。
他拧着眉看了那个沙发一眼。
大概是用木板打的,薄薄的布料覆在上面,看上去就硬邦邦,盛矜与走过去敲了敲,果然发出了咚咚的清脆声响。
他又上下打量一下,这长宽比,这上下落差,别说塞下一个他,那半拉小腿都得拖到地上,大半夜翻个身能直接摔成脑震荡。
这怎么睡!?
盛矜与烦躁地叉着腰,原地来回走了两圈,走过去问苏涸:“那个沙发能睡人?”
苏涸从床上跳下来,点点头:“能睡的,虽然小了点,但我睡觉老实,拿东西挡一下就行了。”
“你……”
还未出口的话直接噎住,盛矜与看着他:“你睡?”
苏涸走到窗边关窗,肯定地说:“是啊,你不是不习惯和别人一起睡。”
盛矜与沉默片刻。
直接拎起沙发上的被子和枕头丢上床。
苏涸一愣,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盛矜与被看得莫名烦躁,偏头撇开眼神说:“我没那么多毛病,少污蔑我,上床睡。”
简直大方的不像他了,苏涸笑了笑,没什么好推辞的,他乐呵呵地抱着他的枕头上床了。
毕竟本来他就是怕盛矜与的一身少爷毛病作祟,不然放着软床不睡去睡硬板沙发,苏涸才不会没事找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