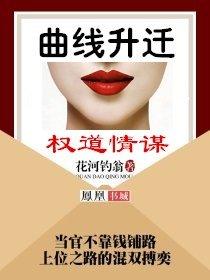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女配以身入局,疯批世子步步沉沦 > 第112章(第2页)
第112章(第2页)
谢余年并不催促。
“他做这些,”过了一会,赵若钦突然开口,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多数是为了太后。”
谢余年眼神微动,但并未打断。
他知道皇帝的人就在门外听着,涉及宫廷秘辛,他也只需要静静地听着就好。
墙上的火把忽明忽暗,将两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面上,扭曲成诡异的形状。
太后初入宫时,只是个小小答应。
若不是有萧旌的帮助,不会在短短几年就坐到皇后的位置。
“可是人的野心哪是能满足的?”赵若钦突然抬头,通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讥讽,“当了皇后还不够,她还想当太后。”
“她并无亲子,”赵若钦的声音越来越轻,“又这么年轻,她要想成为太后。。。。。。”
铁链突然哗啦一响,他挣扎着坐直了身子,“于是就选上了。。。。。。当今圣上。”
谢余年垂眸,袖中的手不自觉攥紧。
当今圣上的生母,是先帝的淑妃,在圣上十岁时就。。。。。。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谢余年声音冷得像冰。
赵若钦神经质地笑了起来,铁链随着他的颤抖叮当作响,“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谢余年一把揪住赵若钦的衣领,将他提起来抵在墙上,“你还知道什么?”
两人呼吸交错,赵若钦的吐息里带着血腥气,“你猜,先帝为何突然病重?你以为淑妃真是病逝?”
曾几何时,他以为自己对萧旌的痴狂是这世间最纯粹的感情,纯粹到可以毫不犹豫地剖开胸膛,将那颗滚烫的心捧到那人面前。
说来也可笑,萧旌也信他。
当年萧旌还年轻,许多事做的还不够老练,留下了不少隐患。
于是便将这些最隐秘的事交给他办。
一颗甜枣,叫他甜了一辈子。
过了一个时辰,谢余年转身朝外走,离开时,还能隐隐听见牢房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呢喃,像是濒死之人的最后忏悔。
“母亲。。。。。。”
谢余年出来后,站在御书房明亮的灯火下,一时间竟觉得有些刺眼。
他向皇帝拱手行礼,“微臣不负所托。”
皇帝脸上的怒气已经消了,换上了那种谢余年熟悉的温和笑容,他亲手扶起谢余年,“爱卿辛苦了。”
平反
谢余年直起腰,走到御书房角落的炭盆旁,伸手烤了烤火,才缓缓道,“赵若钦的话毕竟只是一面之词。。。。。。”
皇帝轻笑一声,打断了谢余年的话,“爱卿是怕朕贸然行事?”
御书房内一时寂静,只有更漏滴水声清晰可闻。
谢余年抬眼,正对上皇帝深不见底的目光。
那里面既没有震惊,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早有预料的平静。
“微臣以为,”谢余年缓缓道,手指在炭盆上方轻轻翻转,有火光在他指缝间流淌,“是时候了。”
皇帝眼中精光一闪,唇角微扬,“哦?”
谢余年收回烤暖的手,“赵若钦所言若属实,背后牵连的恐怕不止一两条鱼。”
他抬眼看向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臣注意到,近来弹劾摄政王的折子,多了起来。”
皇帝走到御案前,指尖轻点其中几封奏折,“这些倒是墙头草。”
“墙头草也有好处,”谢余年挑眉,“如今只需要再添一把火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