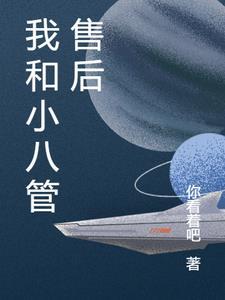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陆队今天捡马甲了吗 > 160170(第19页)
160170(第19页)
月拂站在门口和房间地板保持水平,轻叩了叩房门,“阿姨。”
贺然的注意力凝到门口,声音淡淡的:“小拂,你来啦。”
床边放着一个大亚克力箱子,里面放满了本子,贺然笑的惨淡,“小祯在日记里提到了你。”
“这孩子喜欢写日记,本子还不爱用花里胡哨的款式,跟作业本似的,老土。”贺然挪了下肿胀的小腿,“你看,从小学一直写到初中,高中太忙,没写,一下子就看完了。”
月拂在旁边坐下,贺祯参加工作之后搬了出去,她爸爸有套小房子离市一院很近,只有休息的时候,贺祯才会回来和贺然住。
贺然遗憾道:“早知道,还不如让她跟我住,还能天天见面。”
月拂安静听着,犹豫后还是伸出手,顺着毛衣顺滑的纹理,试图抚慰不平的母亲。
“她同事来过了,向我道歉,她比贺祯大一些,眼睛哭红了,”贺然说:“她伤心就好。”
“小拂,你当时怎么就没赶上呢?”贺然转过头,眼底全是红血丝,直勾勾盯着月拂,“你怎么没杀了他。”
“你是警察,为什么连我的小祯都保护不了。”
月拂沉默,她不能为自己辩解,在失去女儿的母亲面前,自己的痛苦比不过要靠药物镇定的母亲。贺然总要把情绪发散出去,女儿的不幸来自很多人。
两人在全是贺祯的房间里熬着,贺然的话破碎不连贯,在看完的日记里,她随手选了一本,又开始看,企图从随机中抽取出新鲜感。
“你看,初二下学期的,她说抄错你的一道数学题,以为你的也错了,结果是她粗心写错运算符号。”贺然笑道:“我一个当老师的,居然才知道小祯也抄作业。”
“小拂,谢谢你啊。谢谢你给小祯抄作业,这孩子确实不喜欢数学。”
贺然看完这一段把日记合上,并没有将本子插回原来的位置,又随机选了一本,翻到哪看哪,“同学说学校旁边那条巷子的路边摊有好吃的炸年糕,周五放学她在学校门口等你,你说好吃,小祯觉得一般,而且她觉得老板耍酱的刷子没洗过,以后不带你去。”
月拂记得,炸年糕,贺祯要了一串浸红糖的,自己要了个微辣。两个人背着书包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口甜一口辣分着吃,当时贺阿姨在带高三班,压力很大,贺祯索性搬来和自己住,等她们回到家,奶奶刚把饭菜端上桌。
月拂想笑,谁会把背着大人吃路边摊的事写进日记里,她又想哭,贺然很尊重女儿,从来不会翻贺祯的日记。
在初三下学期的日记中,记录很少,有时寥寥两笔只记录天气,还有大段描写是自己转学之后,贺祯聊到了孤独,她在日记里这样写;【今天天气很好,格外想念月拂,她那边是阴天,月拂不喜欢阴天。】
月拂才知道贺祯和班上同学处的一般,她很期待暑假的到来,她可以去京州。
在京州的假期,贺祯年年都来,在读大学开始挣钱的月照,给她们很多零花钱,防止她们俩影响她挣钱,于是在京州很多地方,她们留下过最鲜活的快乐。
月拂都忘了,在自己年少时,原来那样快乐过,而其中大部分,贺祯都在场。
鲜活灿烂的记录,成为横亘生死之间的疮疤。连飞扬的笔迹,再看是一种残忍,贺祯的人生没有随着笔划走进正确的拐角,划出一大笔遗憾。
今晚的风有点大,天气预报未来一周会降温,还会下雨。陆允开车迎着寒风抵达小区门口。
在五十米远的位置陆允看见坐在花坛边的落寞身影,她的身后是在寒风中颤栗的花木,瑟瑟发抖摇摇欲坠。
陆允打开双闪下车接人。
“不知道找个没风的地方等?”月拂整个人是凉的,活人该有的温软被风吹没了一般。
月拂说:“我怕你看不到我。”
陆允没多说什么,搂着人塞进车里。
车载制热被打开,陆允说:“你衣柜里没有厚外套,这两天降温,要回家拿吗?”
月拂才感到冷,她把手心贴在出风口,“奶奶那也没有厚外套,买新的吧。”
现在过了十点,商场早关门了,陆允也不可能这么晚了带月拂去买衣服,“先穿我的,我之前有几件外套,没怎么穿。”
月拂嗯了一声,然后说:“想吃炸年糕。”
“饿了?”
月拂点头。
“到家给点外卖行吗?”
“你会做吗?”
陆允开车撇了一眼旁边吹手的月拂,眉眼淡淡的,鬓角两捋轻盈的碎发乖顺地垂下,模样实在引入怜爱,“回去看看楼下有没有食材。”
到了小区,楼下商超还没关门,陆允把月拂留在车里,进去买了一包年糕一袋红糖。
“怎么突然想起来吃这个?”陆允记得月拂是不吃宵夜的。
“突然想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