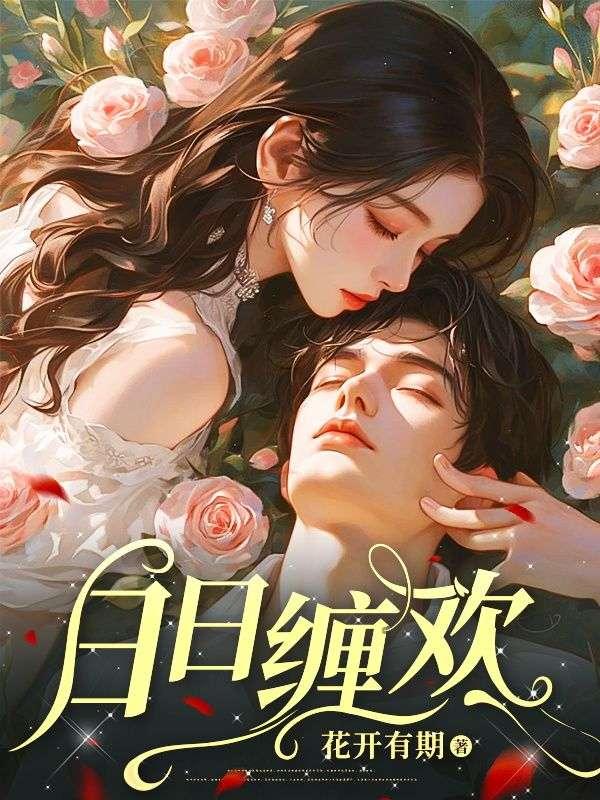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月渡平野 > 第110章 听夏雨梦回初遇(第1页)
第110章 听夏雨梦回初遇(第1页)
第一百一十章
这段日子里,平野每天雷打不动地铸剑,山庄中人渐渐也瞧出些端倪,阿壑这一日总算抽出空来,跟在平野后面,见平野进了院子,他轻手轻脚地上了院墙。
平野利索地换了一身粗布麻衣,手臂上的疤痕刺人眼睛,又听得洪安问:“平少侠,你这半月每天都来,一来就是一整天,消瘦了不少,我和两个徒儿商量了一番,如今这‘别泪’已初具雏形,剩下的不过就是反复锻造了,这活儿你且放心交于我们来做,你好好休息养伤就好。”
别泪?
难道就是那把剑的名字?
可为何取这个名字?
阿壑想不明白,只觉着那尚在锻造中的长剑,剑身颀长,流光溢彩,剑锋锐利,剑柄似刻有祥云盘龙,好不威风。
只是这样的精雕细琢,想必费了不少功夫,从平野那斑驳的掌心就能瞧出来。
平野摇头道:“诸位好意我心领了,可这剑就要成了,我不想半途而废。”
洪安知道这剑用意不单单作以防身,还有定情之物的含义:“既然如此,那咱们也不多加相劝了。”又看看天色,乌云密布,暴雨将至,“不过我总觉着近日有甚么大事要发生了……”
兴许是因着手伤,平野时不时便要停下来休息,脸色也渐渐发白,即便如此,也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阿壑看得久了,心头冒出一个念想来:难道这便是情之所钟?因着这情,才不舍昼夜,不辞辛劳。
不多时,果真下起了雨来,火炉和打铁声都被吞没进了雨水中。
阿壑自院墙上跳下,却不由得浑身一僵。
少年身着一袭绛紫,袍面百鸟争鸣,百花争春。头发高竖,以金丝玛瑙束住,露出一张白净清丽的面容来。鬓边发丝湿润,紧贴侧脸,有些凌乱。
不知在这看了多久。
洪五拿着一把油纸伞跑出来,见到姜渡月,立刻谢罪道:“少主,这雨来得太急,恕属下来迟了。”
细密的雨珠争相落在少年的睫毛上,他一眨眼,又如细雪纷纷垂散。
“无妨。”姜渡月说,“他知道你跑出来了么?”
洪五连忙道:“平少侠专心致志,不曾注意到我的去向。”说着抬眸小心翼翼打量着自家少主,提议道,“少主,既然你每日都要来,为何不进去细瞧……”
每日都要来,守着此处看一会,却总是止步于门槛之外。
姜渡月也不知自己为何如此,明知他挥挥手,平野就会毫无怨言地任他摆布,可瞧着他专心于铸剑时的模样,姜渡月却又发现,自己终归是太过心软。铸剑时的平野,全神贯注,没有与他对视之时的诚惶诚恐,亦没有独处时的怅惘无措,他盯着那剑,仿佛手持那剑,斩尽天下不平事。
和他们初遇那日,别无二致。
说不尽的少年英雄气。
“少主……”阿壑低声呼唤着,“雨愈发大了。”
一把油纸伞又能抵挡住甚么?
姜渡月回过神来,低低地嗯了一声,转身朝外走去,阿壑冲着洪五挤挤眼睛,洪五会意,转身跑回了院中。
不知不觉间,姜渡月没有回到自己的院中,反而走到了那瀑布外的小屋。
这屋子与其说是牢房,不若说是小院,粉白二色蔷薇相继盛放,如今雨水淋漓,更显迷蒙飘摇,雾气四浮,步入仙境一般。
“你回去罢,我在此待一会儿。”姜渡月推门而入,对阿壑道,“不必管我。”
阿壑犹豫片刻,还是转身离开了。
少主心情不佳,做属下的也没甚么办法,回到院中,却见远处的拂香亭内正有一青年,面前摆着一盘围棋,却只有他一人手执黑子,沉默对弈。
正是元讷。